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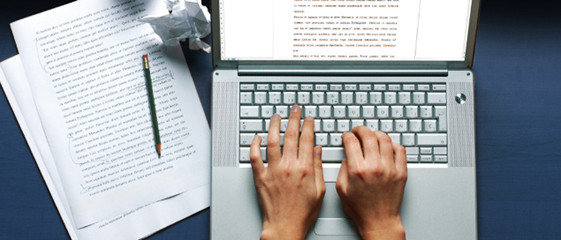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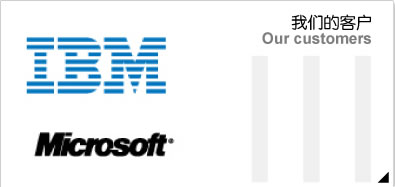
翻译与归化
发布时间:2012-02-23 09:36:44 来源:ACME 转载 字体: 大 中 小
美国史密斯大学教授桑禀华(Sabina Knight)最近发表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小说:论英译中文小说》一文。在英语国家,大学教本科生中国文学用的都是翻译作品。多年下来,她发觉在选材方面有两个惯性问题。一是“量的不足”,二是“值的偏狭”。
桑教授举了一些数字说明“量”的单薄。2004年在美国出版的新小说中,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占3.54%。同年,中国出版社买了3932本美国出版物,而美国出版社买的中文书只有16本。这两个数字的差异说明了一个事实,中译西方小说(尤其是美国的)近十年来成了出版界的“重工业”,言情的、科幻的、古典的、流行的,似乎各家各说在中华大地都有市场。
反观中译英的市道,真不可同日而语。“量的不足”,因为市场需求不大。“值的偏狭”跟量的不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来可供选择的翻译就没有几本,而就题材而言,桑禀华“觉得目前既有的英译中国小说太偏重煽情文学了”。什么是“煽情文学”?桑禀华没有举实例,不过我们自己心里也明白,“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色情暴力的场面着实不少。跟桑教授所说的“有人文视野的中国小说”相比,怪力乱神较易为西方的“一般读者”受落。这正是她所说的“值的偏狭”的理由。
如果中译英作品像桑禀华说的几乎一面倒倾向“煽情文学”,这不会是一种巧合。出版社是商业机构(宗教或政治团体经营的应是例外),在商言商,其商品的设计与制作不可能不受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据桑禀华引的资料,国际出版公司企鹅集团花了10万美元买了姜戎的《狼图腾》的版权出英译本。桑禀华说得有理,这么大的一笔费用对出版社来说是一项很大的赌注,因为译本若以零售价每本15美元来计算,要卖上数万本才能收回成本。除版权费外,出版社所付的制作费还包括广告费、翻译费和零售商的利润等。
英译本《狼图腾》跟原文有多大的出入?原著中的序文和尾声删掉了,内文的篇幅也大见节删。此书的译者是译坛老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相信他当初接到企鹅编辑部的节删指令时,一定觉得有点不自在。他向出版社请示这种“切头去尾”的改动是否恰当,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我们的书,我们已经把它买下来了。”
作者售卖翻译版权给出版社时,可自订一些约则,如说明“本书内容如非得作者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更改”等。姜戎大概没有订下这条规矩。英文版的《狼图腾》所作的改动,看来是依法有据的了。
但有时英译本出现的一些改动,是译者事前跟作者商讨后的决定。葛浩文也翻译了莫言的《天堂蒜苔之歌》。原著的最后一章以一系列批判大蒜“反动”的新闻报道和报纸社论收场。葛浩文大概以西方读者眼光去看,觉得这个收场有点怪怪的,乃写信跟莫言商讨,问他愿不愿意为英文版另写一个结局。莫言接纳了译者的建议改写了最后一章。桑禀华比较了两个版本后,说:“按照葛浩文意见而改写的结尾体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写实和个人的重视。改写前的结尾强调政府的集权控制,相对地小说中的各个人物就显得不重要了。”
葛浩文只给莫言提意见,他并没有“越俎”代作者捉刀。但Evan King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Richshow Boy, 1945)欠的就是这份对原作者的尊重。原著中的祥子在结尾时自暴自弃,变成行尸走肉。译者把这些关键文字都删了。小福子抵受不了妓院恶人的折磨,自杀死了。但译者让祥子把她救活起来:“夏夜清凉,他一面跑着,一面觉到怀抱里的身体轻轻动了一下,接着就慢慢地偎近他。她还活着,他在活着,他们现在自由自在了。”
译者促请作者修订原稿的动机如果不是为了迎合读者口味(“市场经济”),可能就是“假公济私”,以节删或改写的方式来满足私愿。Evan King大概读了不少“花好、月圆、人寿”的中国旧小说,不忍看到苦命的祥子余生孤苦伶仃,动了菩萨心肠,置译者操守不顾,一念之间就让小福子起死回生。
《狼图腾》的英译本大削原著篇幅,最大的原因可能不是为了省成本,而是考虑到作者用以“教化”自己同胞的文字,一旦译成英文,“老外”读者不易消化。商业出版社的运作,不能不优先考虑市场效应。桑禀华的文章提到她曾就英译中国文学的删改问题请教过葛浩文教授。“他非常诚实地告诉我,这是因为中文小说在美国的销路一向不好,所以他以改写原文的手段来向美国的大出版商促销。”简单点说,译者要“引进”一本充满异国情调的外国作品,得先在这本作品做些“归化”(naturalization)的功夫。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文化活动如何“委曲求全”,这应该是个非常贴切的例子。
作者系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
薛仁明:敬字亭
薛仁明
前阵子,我在屏东县文化局讲座,谈“台湾书法困境的文化观察”。其中,提到了《东方早报》有则消息,上海社科院调查申城一地之人文素养,结果,以“90后”的市民最高。我笑着对听众说,要不,请台湾的“中研院”也做个类似调查,如何?
这当然是戏言。因为,不待调查,结果便已昭然。台湾若论人文素养,几乎就是随年龄而递减。在三四十岁,则出现了一波陡降。盖因他们受教育时,台湾进入了李登辉时代,已开始完全资本主义化,从此,逐年庸俗化,更逐年物化,于是,年甚一年,但见政客之媚俗、富豪之夸富,以及影视明星之搔首与弄姿;至于人文素养,当然已无关紧要。
人文素养的逐年递减,固然可伤;但是,台湾文化底蕴之流失,才更令人浩叹。人文素养关乎学识,或可量化,或可调查比较。但文化底蕴不然,那是整体文化环境熏染而成,如根深,如柢固,与学识几乎无关。台湾的文化底蕴,本遍在民间各地;若论其中之最,可推客家老妪。
客家人保守,重礼数,讲规矩,老太太尤其如此。她们总是一身静气,许多年来,排山倒海的欧风美雨,浮躁难歇的物欲狂潮,对这些老太太似乎都无有影响。你若到台湾的客家庄去看,其勤劳俭朴,其恪遵礼仪,还有那最紧要的祭祀不辍,几乎如同千百年来华夏民族的寻常光阴,一样有着悠悠人世,一样有着礼乐风景。这一个个老妪,看似顽固,其实只是理所当然地珍视自家传统。她们厚土深培,植根于古老传统,所以,对比于两岸纠结的读书人,这些老妪底气十足,清朗健旺。
台湾的客家庄甚多,美浓尤其有名。美浓向来文风鼎盛,极重教育。美浓的博士比例极高,校长又特多。此外,他们的传统底蕴,最是深厚。去年暑日,我去了一趟美浓,将入市区,见到有个小小的六角建筑,标示三级古迹,名曰,敬字亭。
闽南聚落也偶有敬字亭,但远远不及美浓普遍。以前美浓人礼敬文字,自幼教导小孩,但凡有字之纸,不可胡乱丢弃,亦不可任意焚毁,必集中于敬字亭,待礼拜仓颉或文昌帝君之后,方可焚烧。
这样子的礼敬,随着今日印刷品之泛滥,当然已极其邈远;但在美浓,还是偶有老妪告诫,有字的纸,别坐!
他们对文字的虔敬,让我想起了《淮南子》所说的“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天雨粟,鬼夜哭”,是真是假,其实无关宏旨;关键是,对于文字的创造,我们的祖先确实有着极深刻之记忆。发明文字,何等大事?!遥想当时,他们既无限欢喜,又不胜惊骇;既期待憧憬,又戒慎恐惧。他们明白,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文字固然可让这个世界光彩纷呈,也可使这世界光怪陆离,更可以使这个世界从此错乱崩解。
文字肇始,祸福未定;我们的祖先不敢有现代人信息爆炸之沾沾自喜,也不敢有现代人对讯息流通之亢奋狂躁。他们只是无有轻佻,只是感得了这成毁之机,因此,诚惶诚恐,虔敬以对。有此虔敬,才可吉祥止止,中国文明也方能绵亘长远,历久弥新。然而,这种虔敬,在百年来中国文字一波波的劫难之后,早已杳然。劫难之一,是过度简化,不仅破坏了造字原则,捣毁了整体意义系统,更蛮横地视文字只是工具,不再有神圣性,亦不复有庄严感。劫难之二,是白话文运动走入极端,过度贬抑古文,弃文言传统于不顾;紧接着,又夸大“工农兵”,极度尚俗非雅,从此,粗暴文字泛滥成灾;即使文化人,即使学者,也常用字草率,遣词无度,甚至,还粗口连篇。
从仓颉到《淮南子》,从《淮南子》再到美浓的敬字亭,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对文字根柢之虔敬,散入千门万户,渗进庶民百姓,遂孕育出一代代清和之人;即使不识字,即使无甚人文素养,也能有美浓老妪那般深厚之文化底蕴。有虔敬,方有底蕴;有虔敬,中国文明也方能新生再造。而今,中国文明初初重建,少数有志之士,已挣脱昔日之粗暴文字,重拾对文字也是对文化最根柢之敬意。他们明白,与其成日忧国忧民,与其整天空谈中国前途,还不如踏踏实实从眼前做起,那么,就先恢复中国文字该有的清净与庄严吧!
作者系台湾知名文化人
林少华:诸葛孔明PK村上春树
林少华
如今村上春树在中国人气倍增,炙手可热,成了时尚文化的符号,成了城市晚报上的关键词,成了出版社以至书店的拳头产品和卖点。作为“村上专业户”,我自然满心欢喜。但欢喜之余,又颇不服气,心想难道国人之中就没有走俏东瀛的文化名人?若论本田松下日立索尼雅马哈等经济品牌倒也罢了,而文化品牌岂容彼国独专其美!于是趁每次东渡之机东张西望凡事留心。尤其每次逛书店或进图书馆,即使着急赶车也必去“中国文学”专柜专架瞪大眼珠子左顾右盼上下扫瞄。贾平凹的《废都》有了,莫言的《丰乳肥臀》有了,陈忠实的《白鹿原》有了,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了……但翻看版次,一般都是几年前第一版印了一次,而初版初印不大可能超过5万册,影响可想而知。卫慧的《上海宝贝》倒是一印再印,据说已卖了20万册。可惜这个实在高兴不起来。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忧心忡忡—担忧日本人产生误解,以为中国女孩见了西洋男人个个把持不住,以为中国女性全都得了“自我殖民化”病症。再往下看,但见金大侠《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武侠全集齐刷刷一字排开,甚是威武雄壮,但销量远不如在中华故土那般势不可挡。据我所知,译成日文的当代中国小说里边,旅英华人作家张戎写的《鹤》—日译本名为Wild swan(《野天鹅》)—卖得最火,出版社美美赚了一把,她本人也曾应邀手持她祖母穿过的“三寸金莲”绣花鞋赴日作过宣传,但那终究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书架上已难觅其踪。
总之,找了半天,很难找出足可与村上春树之在我国相抗衡的人物。这让我怅然良久。于是转而求救于列祖列宗—打量古典文学。这方面的确比比皆是。从诸子百家到李白杜甫白居易、唐宋八大家以至《菜根谭》,简直无所不有,而且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即使我国一般新华书店的古典文学专架也未必如此齐全。四部古典名著就更不用说了。其中尤以《三国演义(日本习称《三国志》,当然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蔚为大观。各种译本(多为编译、改译)和连环画(漫画)琳琅满目。光是横山光辉的60卷本连环画十几年前就已卖出3000万册。读者群一是公司白领,二是学生。没有看过“三国”的大中男生似乎寥寥无几(说得极端点,中国同类学生中看过者恐怕倒寥寥无几了),“三国”每每跻身于男高中生喜欢读的十本书之列。而“三国”人物中,尤其对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推崇备至情有独钟。其最喜欢的情节是三顾茅庐,最感动的场面是星落秋风五丈原—均与孔明有关。据日本青少年研究所一次调查,诸葛亮乃中学生心目中的十位英雄人物之一。关于诸葛孔明的考证历来是日本“三国志”研究的主线,书店中类似诸葛孔明传的书不断有新作加盟,且大多出自名家之手。不但上规模的书店,即使小书店也常可见到孔明手摇羽扇的形象,令人油然涌起“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其实诸葛先生在世时蜀汉与倭国概无交往。他死后四年即公元238年倭女王卑弥呼方遣使至魏,从魏明帝曹睿那里讨得“亲魏倭王”封号和一百枚铜镜。因此孔明知不知晓—虽然据说他无所不知—东海尽头有个日本都是疑问。而今先生却成了彼国家喻户晓之人甚至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在电子游戏机里更是频频得手,杀得曹魏哭爹叫娘人仰马翻。
在“三国”热或孔明热的推动下,日本近年出现了中国古小说和古中国历史题材风潮。就连《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和《说岳全传》也译成了日文。在由日本作家创作的中国历史题材小说里边,宫城谷昌光取材于春秋战国的小说影响最大。《夏姬春秋》、《重耳》、《晏子》、《管仲》……一部接一部推出。其中尤以上中下三卷本的《重耳》风行一时,极为畅销。畅销得我这个来自重耳母国的中国人也每觉匪夷所思。我敢打赌,了解重耳的日本人肯定比中国人多,日本的孔明迷未必少于中国。至少,中国中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我猜想不会是诸葛孔明—是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倒颇有可能。
本文开头说要去日本寻找一位足可与村上君分庭抗礼的中国文化名人,结果遍寻现当代作家而不得。怃然之际,忽然发现诸葛先生在东瀛大放异彩。日本的孔明热,无论持续期间之长还是追捧人数之众,都远非中国当下的村上热所能比—比之村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名人”总算找到了,没有让村上春树独专其美。这诚然令我欣慰,但同时又感到怅惘—难道我们今天就不会再产生像孔明那样有强大文化幅射力的人物吗?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