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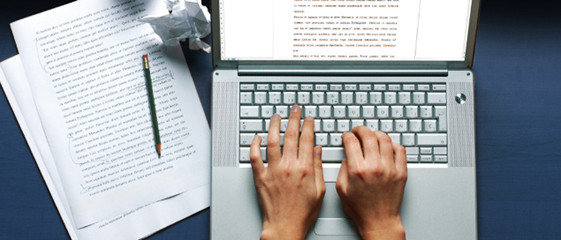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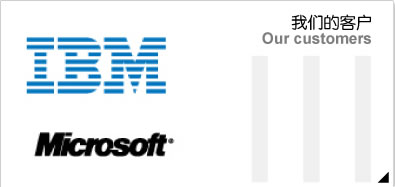
翻译家的悲剧
发布时间:2012-01-29 09:23:49 来源:ACME 转载 字体: 大 中 小
事情发生在多年前的8月
28日。8月28日是瓦西里·阿克肖诺夫[(1932—)俄国当代著名作家。1980年移居美国]的生日。
阿克肖诺夫其时已出版了他的第一批优秀著作如《带星星的火车票》和《来自摩洛哥的橙子》。瓦西里·帕甫诺维奇的大名无人不识,他的名字给复兴俄罗斯散文带来了希望。
阿克肖诺夫交游甚广,过得既像绅士又豪奢。他挣钱不少,可一个子儿都没存下。
生日庆祝会就是按这两个原则来办的。租用文学工作者中央之家整整一个晚上。餐桌设在两个大厅里,一个像巨大的冰斗,另一个像字母“П”,来宾多达数千人,外加一队爵士乐队。
到处摆放着切开的成熟的阿斯特拉罕西瓜和菲利浦·莫里斯牌美国香烟。食物,葡萄酒,伏特加———一切都是优质的。
我从列宁格勒去参加阿克肖诺夫的生日庆祝会,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就你一个?”瓦夏问我。“就我一个,”我回答说。“任尼亚有事儿来不了。”
“那就请和我的日译者坐在一块吧。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我这就介绍你们认识。无论谈什么都行。”
瓦夏把我领到一个根本说不清年龄,戴眼镜,身穿浅色外套,梳着平整的分头的汉子旁边。我们在餐桌摆成“П”字形的大厅里并排坐着。
我们用高脚玻璃杯喝伏特加,佐以上等鲟鱼子和鲟鱼肉。应该找些话题聊聊。
“您翻过阿克肖诺夫?”我问,以便挑起话题。
“是的,”日本人谦恭地说,“十分愉快。两部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和《来自摩洛哥的橙子》。”
“您研读俄国文学很长时间了吗?”
“我毕业于东京大学俄文系。打那时候起便开始翻译。”
“请问,除阿克肖诺夫外您还翻译过谁?”
“我翻了九十六卷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全集。”
“您大概在说着玩吧。”“不,完全不是说着玩。我还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八卷集,别谢勉斯基(俄国小说家)八卷集,冈察洛夫六卷集和许多单行本。”
“这不可能,”我激动起来,给邻座的玻璃杯斟上伏特加。
“怎么不可能?”日本人不动声色地说。“您这就会相信,我没有过甚其词。”
那时候还没有袖珍计算器。日本人除去餐巾,掏出一支名贵的蒙布兰牌钢笔,写上一沓数目字。然后向我解释说:“我五十二年前大学毕业。每天都工作,难得离开家。我用一个特别系数来统计自己的进程。我一年放假两天———我的妻子的生日和天皇的生日。我的定额是———每天六页纸。对,大学毕业后我病过二十-二十五天。这些天我也要算上。现在我把这一切互乘,”日本人边说边凑近了稿纸。
尽管在我看来,他在耍我,但我仍然激动起来。就在我喝酒和吃小食时,日本人算好了他的数学习题,他强调的双重特点的结果,一旦看见这个难以置信的数字,我马上明白过来,他一点也没夸张。我差点想吻他的手,但管住了自己。看见桌子边还有一听装得满满的鱼子,便推给了他。
每当我想起逃避工作,或者在书桌前找不到写作的状态,又或者想到哪儿去时,我总想起这个日本人互乘的那一沓数字。
我国翻译文学史上,专业俄国文学翻译家以汝龙和草婴成就最大,称之为量多质优,毫不溢美。但是,从量来说,比起上文提及的那位日本人,毋庸讳言,两人仍远有不逮。汝龙去世已二十年,他晚年倾其全力译校的《契诃夫文集》,可说是翻译生涯的曲终奏雅。草婴三十年来虽然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集,但也仅得十二卷。两位翻译家除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外,还翻过不少别的俄苏作家的作品,如果出版社要出他们的译文全集的话,大概也就只有三十至三十五卷。是他们不如日本翻译家勤快吗?当然不是;是他们不珍惜时间吗?也不是。汝龙四九年后就弃去公职(他曾当过上海平明出版社的编辑主任),不领工薪,仅以版税维生;上海译文出版社七八年欲聘草婴为总编辑,他却而不就,原因都在惜时如金,视名山事业重于一切。那么他们的翻译量何以会比日本人少一大截呢?
日本翻译家大学毕业后几乎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地摆弄自己的翻译,汝龙草婴一旦卷入“以革命的名义”掀起的各种运动,他们能够独善其身吗?能躲得过这些瞎折腾吗?“文革”中,汝龙藏书被抄,房子被占;草婴下干校,两次险死还生,后期被迫去翻供批判用的所谓内部参考小说,这才是造成他们的人生悲剧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