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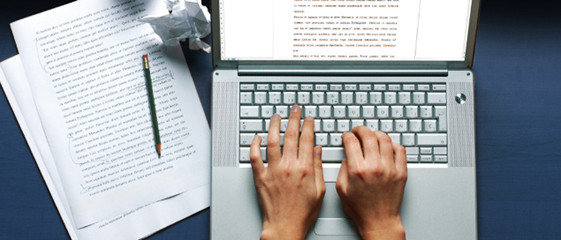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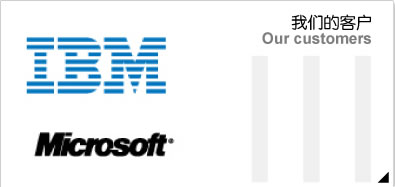
翻译家赵德明:对小说《2666》的赞誉谈不上夸张
发布时间:2011-12-23 14:09:56 来源:ACME 转载 字体: 大 中 小
一
记者:继去年出版《荒野侦探》后,智利作家罗伯特·波拉尼奥另一部代表作《2666》简体中文版近期面世,大陆图书界再次掀起阅读热潮。对这本书诸如“21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超越《百年孤独》的惊世之作”的称誉,即便在听惯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广告词的读者看来,也是有震动效应的。这当然激发了拉美文学爱好者的浓厚兴趣,但多少会让人有些将信将疑。作为拉美文学研究专家、同时又是本书的译者,我想您的阐释会比较有说服力。
赵德明:事实上,这样的赞誉谈不上夸张。我最早在经常去的拉美文学评论网站上发现了这本书,那是在2008年,算来知道得比较晚了。在那时,我就注意到无论在智利、秘鲁,还是西班牙,已经有很多大腕评论家在称赞这部作品。有个叫罗德里戈·富雷桑的评论家就说:“《2666》是全景小说,它不仅是作者的封顶之作,而且是给长篇小说重新定性的作品。”还有评论家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认为,作为全景小说,《2666》既连结和统一起以前的全部作品又大大超越前辈。
记者:您举的这两个评价中,都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全景小说”。我记得在有关巴尔加斯·略萨的演讲中,您也提起过这个概念。
赵德明:没错,略萨一直在努力写作全景小说,他的《世界末日之战》、《天堂在另一个街角》,包括今年出了简体中文版的《坏女孩的恶作剧》等长篇,都在往这上面靠,但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全景小说只有在结构、舞台、立意三方面达到相应的要求,才能名副其实。说到结构,应该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场面宏大、人物众多。《2666》可谓历史纵横,从古希腊一直写到现在,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墨西哥贩毒问题和移民潮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等。牵涉到的主要人物多达近百人,其中有文学评论家、作家、教授、出版家、拳击手、杀人犯、军官、士兵、贩毒分子、警察、乞丐、贫民、妓女……
这么多因素是怎么浑然一体组合在一起的呢?我想多数读者都会有这个疑问。这个疑问本身,触及到了波拉尼奥高超的叙事艺术。《2666》共分五个部分,讲述了五个既独立又彼此呼应的故事。小说以4个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文学评论家开头,讲述他们因喜欢及研究一位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而成为朋友进而成为情人的故事。几人得知阿琴波尔迪曾在墨西哥现身时,便共同前往。这五个组成部分可以独立成章,又有枝蔓开来的大量枝杈形成蓬蓬勃勃的巨型华盖,与巧妙的内在联系和统一轴心一起,构成一棵参天大树。波拉尼奥把情爱、性爱、凶杀、战争、文学研究和创作以及悬疑诸多小说元素自然地糅成一体,尤其是对大舞台和小细节的巧妙结合更令人拍案叫绝。
说到舞台方面的要求,全景小说不能只写一乡一村、不能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故事情节发展要跨到全球几个大洲。这一点,在《2666》中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它直接涉及的国家就有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墨西哥、智利。当然,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立意。立意必须要跳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大洲的局限,站在寰宇之上俯瞰整个人类的高度。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特别是因为在这一层面上达到的高度,一些评论家认为《2666》超越了《百年孤独》?
赵德明:当然,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百年孤独》曾经是20世纪拉美文学的标杆,那《2666》就是对《百年孤独》的超越,因为作者的思想已经飞跃到了2666年,远远突破了拉丁美洲的天地,即站在全人类的现实高度看人性恶的膨胀,更在预见未来。因此,这部作品的意义超出了自身的文学价值,对于研究欧美国家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思潮变化、人类文化价值观念也具有参考价值。
二
记者:总体上看,《2666》给人一种丰富庞杂、光怪陆离的印象,这对读者阅读构成了挑战。我想知道的是,整部小说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
赵德明:《2666》的丰富庞杂,不仅体现在结构、舞台等方面,从读者阅读的角度也有所体现。依我看,对这本书至少可以有5种不同的读法。你可以从了解异国风情的角度看;也可以把它视为了解欧美知识分子的窗口;你也不妨单独地把它看成讲述罪恶、犯罪,连锁杀人案的故事;要把它单独看成一个作家的成长史也未尝不可;更深层次地阅读欧美人跨世纪的心态也非常有价值。
要说有什么核心的主题,我想就是暴力问题。这在《2666》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其中有一个章节写到,在墨西哥的北方,暴力事件频繁发生,200多名年轻妇女被强奸杀害了,还不算每天发生的家庭暴力事件。当然,更重要的是,波拉尼奥在书里揭示了发生暴力的深层原因。在他看来,暴力是人性的邪恶和自私膨胀的必然后果。这包括以公平、正义的名义进行的杀戮,也包括以和平发展、“互利”名义进行的资源掠夺。尤其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性的贪婪与邪恶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在进一步膨胀,在高科技的帮助下,规模大、程度激烈、手段狡猾的大量犯罪事实,都一一证明了人类的贪婪、疯狂和残忍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了自我毁灭的新高度。严重的是,人类还没觉醒,还对纸醉金迷的生活津津乐道。
记者: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以马尔克斯等拉美文学四大主将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可以说已经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2666》在何种意义上克服了这种潜在的影响,并有自己的突破和创新?
赵德明:你提到了一个关键命题。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吸引读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颖的表现形式。但任何东西过了头就过犹不及。有些作品的语言,就变得过分离奇、混乱、让人难以卒读,其实相当于在变相地排斥读者。针对这种现象,波拉尼奥提出,要对表现形式承担风险责任,要讲道德,要考虑社会效果。当然,他其实并没有简单地遵循拉美作家的写作范式,他既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也不是巴洛克风格和民族主义者,没有一个标签可以容纳他,他的文字充满想象力,在语言表述方式上都十分讲究,注意简洁、明快和节奏。
记者:可以想象,翻译《2666》是一次高难度作业。
赵德明:这么说吧,我刚知道这本书,当时就非常想看。但因为在青岛教书没能第一时间找到。直到2010年上半年,出版方希望通过北大为这本奇书找一个中文翻译,青年老师们一致推荐了我。等我拿到原著时,才真可以说是圆了三年的梦。
不过,真到了着手翻译这本书,我就知道自己是在啃一块硬骨头。我先是用8个月的时间,完成近70万字的初稿。又用2个月的时间修改和润色,最终交稿。整个过程如同长征,要一步一步向前走,尤其是翻译到第500多页的时候,很有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感觉。你看我们都在说《2666》了不起,了不起在哪里?部分就在于作者广征博引。除了文学本身,书里还写到了数学、海洋生物学、心理学、战争史等等。翻译时,我手边全是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各个语系的词典。这些词典不是偶尔翻阅,而是须臾不可离开。此外,还要经常用上互联网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百度。即使如此,在《2666》中还存在大量美洲方言。于是,我托友人专门购买了原文的《美洲方言用语词典》,共有2333页!没有这些查询手段,我恐怕很难攻占这个当代文学高地。
然而,仅仅是搬运工具书解决不了书中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暴力问题。这是作者通过5部长篇故事要探索的问题之一。围绕着暴力,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质问。比如,二次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在屠杀犹太人时为什么表现得那样“冷血”?诸如此类问题,就迫使我在翻译的同时不得不思考人性中的兽性成分:贪婪、凶残、狠毒、疯狂……这些问题仅凭简单的阶级分析已经不能解释了。为此,我不得不看一些人类文化学和生态学的书籍,但依然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比如,人类道德问题。所以,它迫使我对半个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和思考。
三
记者:您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也提醒我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很多时候恐怕只是孤立地看拉美文学现象。如果要真正理解拉美文学,就迫切需要对其做一个整体的打量。
赵德明:那是当然。我们的问题在于,只是忙着上课,搞翻译、研究,却从未想过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整个拉美文化,把其中的历史因素,基本特征搞搞清楚。比如,我们知道拉美作家的很多作品都在国外打响,这在拉美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有没有深入思考过?你看波拉尼奥的作品,是在西班牙出版的,在美国获得真正认可,形成显学是在他的祖国智利。智利有一家私立大学,就专门给波拉尼奥开了个研究室。他们围绕波拉尼奥开国际会议,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红学研究中心”的文学组织。马尔克斯的情况也是这样,《百年孤独》是先在欧洲红火起来的,然后回到哥伦比亚,马孔多原型的海边小镇上的人一看,马尔克斯写的都是当地的真人真事,这一下就被认可了。
略萨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我在翻译他的作品的过程中,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拉美那么多作家里面,为什么略萨能脱颖而出?我的感觉是,这与他到了欧洲,在创作上受到启发、另辟蹊径很有关系。其实,翻译略萨的作品,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就是迫使我不得不查阅和他的作品相关的英美文学流派的作家。比如,略萨早年非常崇拜萨特,我就得了解法国文学。因为,对这一块我了解甚少,只好问学长柳鸣九,还有其他法语专业的老师。这方面问题问得多了,我就自然而然伸到了法国文学领地。也是在这过程中,我接触到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我意外地发现,参与这一文学运动的人中,有不少竟然是拉美作家,比如古巴的卡彭铁尔、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等等。他们都直接到了巴黎,在那里聚集创作。实际上,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法国写作完成的。
还有一个背景,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拉美作家,除了他们本国、本民族的语言外,掌握三四门外语是平常事。他们一般都通晓英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语。这和拉美文化的特点很有关系。所以,要真正理解拉美文学,不仅要把拉美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还要放到世界文学,至少是欧美文学的背景下来打量。
记者:联系到波拉尼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他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国际主义,或者说是世界主义写作的范本?
赵德明:我想,波拉尼奥显然意识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里,作家,尤其是四海为家的文学家,肯定是(也不得不是)放眼世界的,囿于乡土一隅就很难走向世界了。事实上,他的写作之所以能完全告别上世纪70年代拉美实验小说的形式臃肿,恐怕也与他对时空认识的改变以及电脑写作技巧的应用不无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敏感的作家都会感觉到,就“乡土写乡土”是非常狭隘的,因为全球一体化的大潮席卷每个角落,不站在全球高度看乡土,肯定说不清楚局部与全球的变化。所以,对于作家来说,孤立地看待本国、本民族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困难了。
记者:如您所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多作家都已经意识到要拓展写作视野。但实际的情况是,这种普遍的认知和具体写作实践常常是脱节的,尤其是中国作家中的大多数,依然在既有的小圈子化的写作模式中打转。您认为,波拉尼奥的写作给出了什么启示?
赵德明:实际上,波拉尼奥的写作,也是从一己的切身经验出发的。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从青年时期热情支持智利左派政府,到军事政变后被捕入狱,到逃亡国外,流离四方,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在贫困中,而且疾病缠身,他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顽强的写作,非要把胸中的郁闷倾诉出来不可,因此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自传的成分。但我们不能不意识到,波拉尼奥如此痛苦的个人经历又是社会和时代强加给他的,写作时自然离不开“集体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经历中,长时间生活在守夜的门房里,采摘葡萄的果园里,小区商店里,天天是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因此用不着深入生活就可以直接获取“集体经验”。所以,他很清楚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这种清醒的认知,让他打破了类似个人与集体、民族与世界等等很多界限。
记者: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波拉尼奥的创作,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这种观念已经彻底过时了?
赵德明:这个问题点到枪口上了。长期以来,这句话都被概念化地简单理解,从来没有人很好地解释过。我们首先得问问,是民族的什么?我们可以说,经过时间淘汰后留下来的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粹,但在接受的过程中,是否就可以变成世界的,这是要打问号的。比如,《红楼梦》够经典的吧,但有一次在巴西利亚大学看这个戏,我注意到很多观众看到一半多一点就慢慢退席了。因为他们看不懂。巴西人表达感情,一上来就是拥抱、接吻,就说“我爱你”。你叫他们怎么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所以极尽婉转的感情表达方式。就拿京剧来说,我们讲,当年梅兰芳一到了美国,怎么受到欢迎。但你要明白,它在美国的观众,到底也是高层的,极少数的,京剧到底也没有在美国变一个洋京剧出来。
所以,我们要思考,民族的什么,是可以变成世界的。很显然,像电脑、手机这样的机器硬件,是很容易从个别地方开始,转而变成世界的。当然,还有音乐、小说等艺术形式。比如,我们本来是没有话剧的,从西方传进来以后,就开始有了中国舞台的话剧,但从成就上来说,还是远不如发源地。但不管怎样,一些包含人类共通情感和经验的艺术形式,的确是可以变成世界的。另一个可以实现这种转换的,我看就是智慧,智慧能突破地域限制。比如,咱传统文化中孔孟、老庄,尤其是《孙子兵法》的一些思想精髓,全世界都在用。但反过来说,民族中一些狭隘的东西,那不但不是世界的,而是应该被彻底否定的。(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