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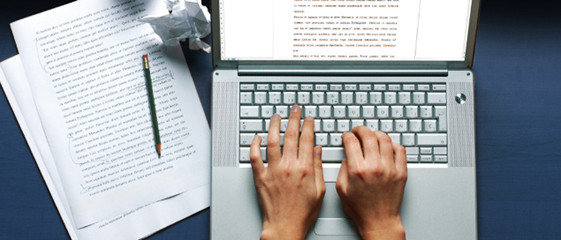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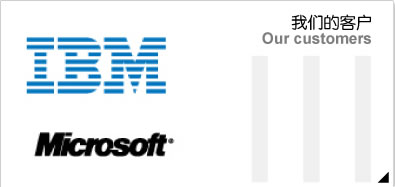
译者赵德明谈翻译《2666》:我读了"老年进修班"
发布时间:2011-12-16 09:00:53 来源:ACME 转载 字体: 大 中 小
《2666》西班牙语原著共有1125页。接受了翻译任务之后,我先把全书看了一遍。第一个感觉是,这是一部用西文写出来的《清明上河图》,特点是篇幅长、场面大、人物多,涉及到历史、哲学、数学、海洋生物学、社会犯罪等方面。作者波拉尼奥对智利、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风土人情都有生动细致的描写。尤其是上述国家里人物的心态、性格、语言特点,作者都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都耳熟能详,仿佛在描写自己的亲朋好友。特别是他塑造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其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令德国文学界拍案叫绝,甚至出现对号入座的现象。一个智利作家如此熟悉他国的文学和历史,实在叫人佩服。
令人佩服之余,麻烦也来了。波拉尼奥的广征博引给才疏学浅的译者提出了一个大难题: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我需要重新学习!于是赶紧拿起了“急用先学”的武器。在翻译《2666》的10个月里,我经常查阅的工具书有:《德汉词典》《法汉词典》《全息英汉词典》《意汉词典》《新西汉词典》《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我,这些词典不是偶尔翻阅,而是须臾不可离开。此外,还要经常用上互联网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百度。即使如此,在《2666》中还存在大量美洲方言。于是,我托友人专门购买了原文的《美洲方言用语词典》(2333页!)。没有这些查询手段,我恐怕很难攻占这个当代文学高地。
但是,仅仅是搬运工具书解决不了书中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暴力问题。这是作者通过5部长篇故事要探索的问题之一。围绕着暴力,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质问:为什么书中的欧洲教授对暴力持冷漠态度?为什么书中的智利教授对暴力不得不采取容忍的态度?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敢于见义勇为,但又半途而废?为什么墨西哥警方对连环杀人案件要么不作为、要么办案不力?为什么杀人犯如此嚣张?为什么走私贩毒活动愈演愈烈?二次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在屠杀犹太人时为什么表现得那样“冷血”?前苏联的肃反运动造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恐怖气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那样剑拔弩张?仅仅这一系列问题就迫使我在翻译的同时不得不思考人性中的兽性成分:贪婪、凶残、狠毒、疯狂……这些问题仅凭简单的阶级分析已经不能解释了。为此,我不得不看一些人类文化学和生态学的书籍,但依然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比如,人类道德问题。如何评估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中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呢?经济很发达,文化很发达,为什么书中人物的道德觉悟如此低下?三位欧洲教授在伦敦乘坐出租车,由于政见不合,居然对司机大打出手。文明呢?礼貌呢?教养呢?如果说这是文学人物,那么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欺诈行为应该做何解释?难道他们没钱?难道他们没文化?都有。就是没有公德心,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利欲熏心让当今世界的许多政客、大亨以及各种权贵势力集团操纵各种舞台谋取私利,上演了种种尔虞我诈的丑剧,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有什么力量来约束他们贪欲的膨胀呢?没有。法律、舆论监督要么是一纸空文,要么是他们的工具。更不要说军队和警察了,那是他们巧取豪夺的鹰犬。《2666》的第四部分有大量事实可以为证。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实,为什么许多人置若罔闻呢?这是值得人深思的。它迫使我对半个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和思考。
更值得我深思的是,在经济发展和信息时代的今天 ,为什么《2666》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在作者那里,2666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人类灭亡的时刻表。难道发展经济、科学和教育不是人类的出路?波拉尼奥是2003年去世的。2008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从而引发了全球性危机,至今没有摆脱出来。这场危机中金融系统的信用和政府公信力下降,说明一系列观念、机制、体制和制度的危机,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没有回答出造成这些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没有回答出这样的问题:谁来拯救和洗涤人类的罪恶呢?《2666》在这个意义上发出了警报:人类自相残杀,同时又毁灭自然环境,其未来就是自我灭亡,没有别的出路。这样的判断是不是过于悲观了呢?那就要看看人类的聪明才智能不能放在真诚、友爱、同舟共济、善待自己和地球一切物种的发展道路上了。
但《2666》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它的成功依靠的是故事情节、人物的言行、喜怒哀乐的表现。书中没有半点说教的味道。无论马德里、巴塞罗那、巴黎、伦敦、罗马、柏林、纽约还是墨西哥城,作者写出来的景物都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波拉尼奥真是个高级导游,带领读者玩遍了上述城市。我在翻译时,因为去过马德里、巴塞罗那、巴黎、伦敦、纽约和墨西哥城,所以有意做了比对,发现的确准确无误、翔实可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对人物的刻画与塑造中,波拉尼奥极大地发挥了艺术想象力的作用。其中主要人物就多达二三十人,有教授、作家、出版家、政府官员、军警、议员、记者、商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土著人。波拉尼奥对这些人物都有细腻的刻画,其中有的人物是他不熟悉的,例如,二战中,一个德国铁路站长奉命杀害犹太人,他动员了14岁左右的少年组成行刑队,为了麻痹这些孩子的良知,他让孩子们喝烈性酒,然后发放枪支弹药,训练杀人技术,最后开往刑场。波拉尼奥是1953年出生的,不可能亲历现场。但凭借史料和想象力,作者很成功地表现出法西斯杀人的冷血场面(参见译文)。显然,作者很明白细节与全局的关系:具体人物和场景的描写水平决定全书的质量;而只有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才能在谋篇布局时注意到一个棋子位置存在的意义。这种大舞台与具体角色的结合是一些拉美作家努力追求的全景式小说的特点之一。
全景式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对乡土、地域、民族文学观念的突破。这与波拉尼奥等一批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的亲身经历有密切关系。以波拉尼奥为例,他1953年出生在智利,20岁时赶上了智利军事政变,许多左翼青年作家被迫流亡海外。波拉尼奥就辗转到过古巴、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那是一段苦日子,更为痛苦的是思想信仰上的迷惘。在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纷纷改制的90年代,这些作家已经是中年人了,他们原来的信仰模式被一一摧毁。他们的精神近乎崩溃的边缘。怀疑一切成了他们观察社会与人生的惟一尺度。进入21世纪后,这种怀疑态度愈加深刻。尤其是在西方连续发生社会、经济和文化危机之后,他们的认识上升到了从人类高度看人生。高科技手段对这样的认识起着促进和推动作用。科学帮助人类看到自己的渺小、自己对自然的破坏和自己的孤独与浅薄。高科技手段还帮助作家找到了快速、便捷的表达方式。《2666》的篇幅虽长,但是叙述节奏很快,语言简练,完全告别了上世纪70年代拉美实验小说的形式臃肿,恐怕与作家对时空认识的改变以及电脑写作技巧的应用不无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觉得就“乡土写乡土”是非常狭隘的,因为全球一体化的大潮席卷每个角落,不站在全球高度看乡土,肯定说不清楚局部与全球的变化。最近看拉美报纸,有一位评论员说:“中国千万别打喷嚏,否则全球会感冒的。”无独有偶,西班牙一家报纸明确表示“不希望中国放慢发展速度”。其实,全球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早就形成了。孤立地看待本土问题或者仅限于维护本土利益是越来越困难了。作家,尤其是四海为家的文学家,肯定是(也不得不是)放眼世界的。囿于乡土一隅就很难走向世界了。
翻译《2666》的过程如同长征,要一步一步向前走,消耗体力,磨练意志。尤其是翻译到第500多页的时候,很有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感觉。但我不是西西弗斯,不是小伙子,而是老头子。只能笨鸟先飞就是了:早起一点而已。起床后,打开电脑,看原文,查词典,从词义到整句、整段的意思,逐一分析和思考,想出来恰当的中文,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进去。日积月累,经过8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近70万字的初稿。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修改和润色,最终交稿,自我感觉尚可。这10个月的劳动也并非天天经受磨练,也时时有跟随作者神游欧洲和美洲的神仙感觉,也会为作者面对苦难的沉重感而沉重,也会为作者的知识渊博而折服……现在看来,10个月的劳动中,我的确感觉到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我给这一次的翻译、学习过程起了一个名字:老年博士后进修班。但是,我还没有毕业,还在继续翻译波拉尼奥的其他作品。小车不倒只管推吧!
译 文
警察局长、我(铁路站长、德国纳粹分子-译注)的一个秘书和我的一个司机上楼来我办公室。我怀着不祥的预感等候着他们。我记得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坐了下来(司机站在门口);不用他们开口,我就明白了这交办的任务(指大批杀害犹太人-译注)对他们的伤害到了什么程度。我说:总得干点什么吧。
那天夜里,我没回家睡觉。司机开着车,一面抽着我送给他的香烟,一面在村子里静静地转悠。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睡着了,我盖着毯子,梦见儿子喊着:前进!前进!永远前进!
醒来时,感觉四肢麻木。到达村长家里时,是凌晨三点钟。起初,没人给我开门。大门差不多是我用脚给踹开的。接着,听见有人犹犹豫豫的脚步声。是村长。他问:谁呀?我以为是银鼠的声音呢。那天我俩一直谈到天亮。到了星期一,警察没把扫地的队伍(由犹太人组成,以扫地的名义拉到荒郊野外枪杀—译注)拉出村外,而是等着踢球的孩子们出现。后来,警察给我带来了十五个小孩子。
我让警察把孩子们送进村公所会议厅。在几个秘书和司机的陪同下,我到了那里。我一看见孩子们是那样脸色苍白、那样消瘦、那样需要足球和烧酒,就非常可怜他们。他们不像是孩子,更像是一动不动的骷髅、一副皮包骨、有口气的一把骨头。
我告诉孩子们,面包会有的,烧酒会有的,香肠会有的。孩子们没有反应。我把烧酒和食物的诺言又重复了一遍。还补充说,还可能有东西让他们带回家去。我解读他们的沉默就是赞成我的话。接着,送孩子们上了一辆大卡车,送他们去洼地(行刑场-译注),陪同的有五名警察,还装上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警察告诉我,这挺机枪是刚刚换来的新枪。然后,我命令其余的警察带着四个武装农民(是我强迫他们参加的,否则控告他们长期欺骗政府)把三支完整的扫地队伍押送到洼地去。还下令:任何犹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老皮革厂(犹太人临时住地-译注)。
下午两点钟,押送犹太人去洼地的警察回来了。大家一起在车站酒吧吃饭。下午三点,他们押送另外三十名犹太人去了洼地。夜里十点,押解人员、醉酒的孩子们和监视、训练孩子们的警察,统统回来了。一个秘书告诉我:一切顺利。孩子们很努力……
——赵德明译波拉尼奥《2666》
(赵德明)
赵德明,1939年出生,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是最早把秘鲁、西班牙双重国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译成中文介绍给中文读者的中国西班牙语文学研究者。译作有《城市与狗》《情爱笔记》、小说方法论《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又译《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文论集《谎言中的真实: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回忆录《水中鱼》,主编中文版《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