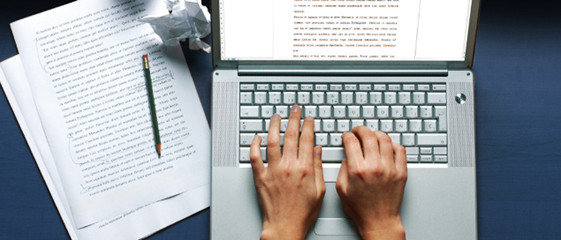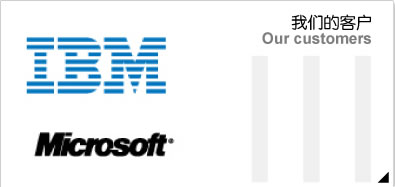李笠:诗人,翻译家。1961生于上海,1979年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系,1988至1992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瑞典现代文学,现供职于瑞典作家协会。出版有瑞典文诗集《水中的目光》、《时间的重量》、《逃》、《归》、《栖居地是你》等,另有中文诗集《金发下的黑眼睛》。除写诗外,他翻译了大量北欧诗歌,其中包括2004年获“新诗界北斗星奖”的
瑞典文学译介太少
记者:优秀的瑞典文学,目前在国内的译介情况如何?
李笠:还是太少。似乎只有斯特林堡,诗歌有一点,《长袜子皮皮》作者林格伦的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作者拉格洛夫有一些。那么小的语种,从事瑞典语文学翻译的人还是太少,实际上瑞典作家的层面是很高的,有几个特别好的散文家至今没翻译过来。抛开文字不谈,中国作家很少去研究问题,瑞典作家会很严肃地去考察一个问题,从来不会想当然。
记者:除了特氏的诗歌,你还会继续做译介工作吗?
李笠:会的,我要把中国诗歌翻译成瑞典文。实际上我已经做了,把麦城、西川的诗歌翻成瑞典文,也陆陆续续翻了一些王家新的诗。
记者:在你看来,把中国诗歌翻译成瑞典文更重要,还是把瑞典诗歌翻译成中文更重要?
李笠:目前好像是把中国诗歌翻译成瑞典文更重要。因为我们有不少值得去翻译的好诗人,包括他们诗歌呈现的中国社会,都值得介绍到国外。
记者:在诗人和翻译家这两个身份中,你更看重哪一个?
李笠:当然是诗人。诗是最高的,翻译只是翅膀。
我在写“李笠”的传统
记者:跨语言写作通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克服了很多困难,总算学会了用另一种语言来写作,等写到一定程度,还是会碰到到底该把自己归入哪一个写作传统的困境。你的创作存在这样的困境吗?
李笠:其实,很难说我用瑞典文写诗顺利过。那就像小孩写汉字,一笔一画、一字一句都要花力气,写得很慢,有时甚至会发生词不达意的尴尬,有点像戴着镣铐跳舞。写到后来,发现如何写,写入哪一个传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用瑞典文只能写生活的当下;而过去,我的背景, 整个中国文化,又怎么用另一种文字展现出来。
在写关于母亲的第六本诗集《源》那里,我找到了出路:先用中文打底稿,然后用瑞典文修理。一首中文诗,变成瑞典文,常常会变短。一种热胀冷缩的原理40摄氏度的上海夏天变成了20 摄氏度的斯德哥尔摩。10行变成了6行。瑞典文的硬冷,直接和逻辑性,精准了中文的意象,简约了汉诗的铺张, 淡化了南方的绮丽。汉语养育了我的诗,而瑞典语则赠予了我的思。我在写自己李笠的传统。
记者:汉学家顾彬曾说,中国作家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能精通一、两门外语。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李笠:顾斌显然在捉弄国内那些自信力不足想讨好欧洲人梦想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这个德国汉学家的观点浅薄,充斥着欧洲殖民主义老子天下第一的恶态。精通一、两门外语并不是成为大作家大诗人的唯一条件,或万无一失的保障。不错,在欧洲,一个作家一般至少都会两三种语言。但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每一种欧洲语言(除了英语)都过于狭小,必须借助别的语言来才得以生存,北欧最大的语言瑞典语只有900万人讲(不到讲上海话的人的一半)。所以,他们要理解世界,与世界沟通,就必须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因为多一门外语就多一扇窗户。国内目前有不少好的诗人和作家,有的既是翻译家,又是诗人。而这种现象将来会越来越司空见惯。
“诗人很穷,但地位最高”
记者:在瑞典,诗人的生存现状如何?诗歌处于何种地位?
李笠:在瑞典,诗人很穷,像特朗斯特罗姆这样的大诗人也很穷,只住在两室一厅的公寓楼里。但诗歌地位比所有的权和利都高。一个政治家,一个畅销书作家,一个诺贝尔奖评委委员都梦想成为特朗斯特罗姆这样的诗人。因为他们相信诗是语言最高的形式,人都想诗意地栖居。
瑞典人读诗歌的比例比中国要大,各大报纸会有诗歌评论。每天十二点,电台当当当敲钟之后有“每日一诗”。有时候朋友听到就给我打电话,说“李笠,今天有你的一首诗啊”。然后电台给你一千块钱。还好,诗歌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间还有位置。
记者:在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国家,读者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如何?
李笠: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是世界平均人口阅读诗歌最多的国家。在欧洲,一般读者读诗歌的水平和修养,比诗人还高。中国教授一般不看现代诗;欧洲一流的人才写小说,写诗歌,写不好的,就写评论,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