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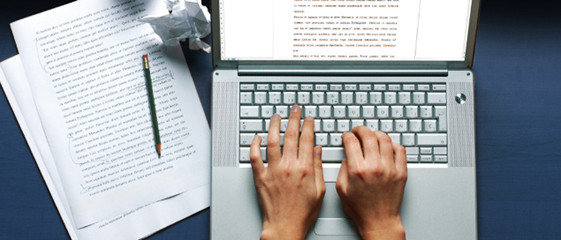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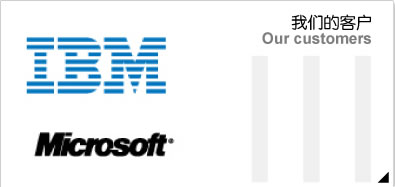
老翻译家忆改革前饥饿:豆渣成救命宝物
发布时间:2011-11-11 10:27:54 来源:ACME 转载 字体: 大 中 小
[导读]我的家母和年幼的弟妹之所以能挺过来,没有出事,主要是沾了豆渣的光。原来他们住在一家酱品厂的宿舍,豆渣乃制作酱品时的下脚料,当时则成了救命宝物。

大跃进宣传画
饥饿记忆
我幼时在老家县城读初中。学生大多家境贫寒,享受着每月数元的人民助学金。一日三餐,都是几个人围在一起,蹲在地上进食。自然是粗茶淡饭,但求一饱。偶尔路过教工食堂,但见我们孙老师正专心致志地对付面前的那一小碗红烧肉。好生羡慕哎。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享用到这样的一碗肉就好咯。孙老师是教语文的,在下就这么点儿出息,当初老师如何给我们传道授业,释疑解惑,几乎全都淡忘。唯独那一小碗红烧肉却牢牢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后来到省城上高中,就餐条件略有改善,有正儿八经的学生食堂,饭菜也比原来丰盛。八个人一桌,就餐时需有人来分菜,比如早餐的花生米就轮个数,绝对公平。荤菜很少,川人把吃肉叫做“打牙祭”,一周也就那么一次。最有趣的是,每逢打牙祭的那天(一般是中午),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围挤在一个大木桶旁边,目的是捞到一点“油面子”,就是煮肉汤表面上的那层油水。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学生大多穿草鞋,甚至打赤脚。宿舍里蚊虫肆虐,有人连蚊帐都置办不起,用所谓的头罩代替,一觉醒来,头部早已挪出罩外,饱受蚊虫叮咬。所谓的床,没有床板,只有几根木条,也没有褥子,把床单直接铺到竹质的笆笆片上,就算床铺了。
及至到北京上大学后,情况方大为改观。住的是楼房,每层有卫生间,冬天还有取暖设备。至于说到伙食,简直就如登天堂。顿顿见肉不说,且分文不花。因为师范生全部享受人民助学金。1957年(大学三年级)赴中学教学实习期间,一早一晚仍在大学食堂用餐,饭菜比平日丰盛,中午在中学的教工食堂就餐,档次更高,多为小炒。照这样下去,赶上孙老师那个水平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了。
按理应该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谁知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反而是每况愈下。为什么呢?说来话长。我因年幼无知,误中“阳谋”,后受到“宽大处理”,发配边陲,工资扣发,只给一点生活费。当时的全部“家当”,除了一床被子、几件换洗衣服,就只剩下离校前到废品收购站买的一只竹箱,实际是个破篓子,里面放了几本书。家中老母和弟妹原本盼着我挣钱养家,如今我已是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我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多年之后仍然家徒四壁,至于孙老师当年的那碗肉,早已是可望而不可即。
头两年虽然艰苦,还可每天混个肚儿圆。到了“低标准,瓜菜代”的年月,可就窘态毕露了。我供职的地方,原本也是“天下黄河独富一套”的米粮仓,秦汉以来即实现黄河水自流灌溉,旱涝无忧。这时居然也闹起了所谓的“严重自然灾害”。原本每月三十斤的粮食定量一度缩水至二十一斤。副食品奇缺。难耐的饥饿使人再也顾不得什么尊严、脸面,堂堂大学老师当众舔碗、提暖壶到食堂灌面汤之类的事情,已是司空见惯。我们也开始吃起榆树叶之类的“代食品”。
我仗着自己年轻力壮,仍是天天加班,终于得了浮肿病。有的好心人甚至怕我顶不住了。当时物资匮乏到了极点,连饭碗也成紧缺商品,就用废罐头盒代替,打回菜汤来,加点酱油膏,再放到火炉上咕嘟一阵,似乎这样就可以增加一点营养。加班加点,仅可得到几个土豆之类的“犒赏”。
其实我要算够幸运的了。因为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老家,更是饿殍遍地。城镇居民的口粮一度降至每人每月19斤。农村的情况更为严峻。我的祖母和外婆原本身体硬朗,这次都未能挺住,先后病故。家母和年幼的弟妹之所以能挺过来,没有出事,主要是沾了豆渣的光。原来他们住在一家酱品厂的宿舍,豆渣乃制作酱品时的下脚料,当时则成了救命宝物。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举国上下痛定思痛,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扭转颓势。1963-1966年,全国情况大为好转。谁知肚子刚刚填饱没两天,又开始了新的折腾。这次是长达十年的“文革”,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四川人吃上了兰考的粮食。原本盛产小麦水稻的塞上江南,也居然开始调入高粱米、玉米等粗粮,面子丢尽。副食供应日趋紧张。
我因情况特殊,更显捉襟见肘。有一次去托儿所送饭,让工宣队队长(曾任海军副司令员陶勇中将的警卫员)碰见,他执意要看看碗里的东西,看完则大吃一惊,当场把我“熊”了一顿:“这怎么行呢?下一代啊!”原来我送去的东西与众不同:一碗只有几片白菜叶的面条里,见不着一星半点肉末蛋渣。孩子瞅着小伙伴碗里的鸡蛋羹,甭提有多眼馋了。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情,孙老师要么已经作古,要么也已七老八十,他如果知道自己当年的弟子居然穷困潦倒若此,不知会作何感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对而言,1956年可说是国人生活中一个太平年份。1957年开始折腾(反右派斗争),人人噤声;1958-1962年大折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饥荒),元气大伤;1963年又开始折腾(农村和城市的四清运动),草木皆兵;1966-1976年超级大折腾(“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二十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105岁老人周有光曾经现身说法:“我在北京,是政协委员,应该算是特殊阶层了,但花生米都吃不到。我家里面有母亲、孩子、几个保姆,粮票都不够用。人家说政协有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可以同夫人一起去吃。我们就经常去,很滑稽的是,每天碰到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生产停滞,物资匮乏,不降低才怪。
假如没有后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孙老师面前的那一碗肉,我辈怕是今生今世也无缘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