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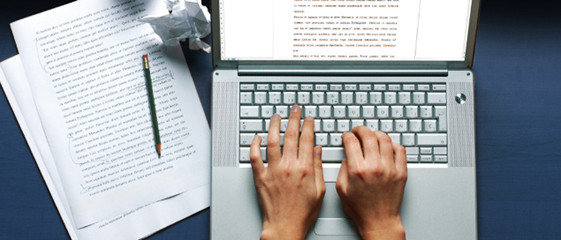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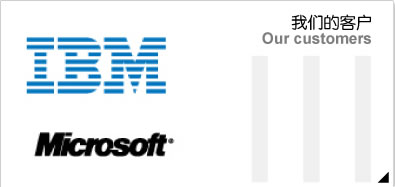
翻译家蓝英年:知识分子的骄傲,在于遵从良知
发布时间:2011-11-08 08:37:47 来源:ACME 转载 字体: 大 中 小

蓝英年,俄语文学翻译家,译著有《滨河街公寓》(合译)、《亚玛街》、《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日瓦戈医生》(合译)、《邪恶势力》(合译)和《塞纳河畔》;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苦味酒》、《回眸莫斯科》、《从苏联到俄罗斯》和《蓝英年随笔选》。(记者 孙纯霞 摄)

今年《捍卫记忆》出版。对于那些怀念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这本书仿佛击中了某种文字的乡情,久违的文字,久违的蓝氏译笔。
1933年出生的蓝英年先生,是俄罗斯文学的点灯人,他翻译俄罗斯文学,也有意识地在俄罗斯文学中,寻找着关于人性的尺度,关于真理与价值的尺度。1989年,蓝英年应邀去苏联教授汉语,刚好目睹世界当代史上最大的变革过程,苏联解体,之后他的兴趣就从俄罗斯文学转移到历史上,并写下大量思想随笔。
利季娅的《捍卫记忆》这本书与蓝英年有近半个世纪的情缘。1958年,蓝英年被下放到青岛一个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偶然读到报纸消息,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作协。那时他尚不知帕氏何人,通过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亲友,拿到帕氏的《日瓦戈医生》俄文版,才知帕氏的伟大,几年之后蓝英年与张秉衡合力将《日瓦戈医生》译成中文,成为经典译作。
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作协的那个房间,正是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的房间,“如果想想当年被开除的人中有左科琴和阿赫玛托娃,有被开除后去世的帕斯捷尔纳克,有不久前被开除的索尔仁尼琴……我感到骄傲的是你们用对待他们的手段对待我”,利季娅的这段话被蓝英年多次引用,这是有血性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骄傲。
2008年,利季娅的女儿,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联系上蓝英年,并确信翻译过帕氏作品的蓝英年,定能知利季娅作品的价值,将其翻译好。蓝英年则早已期待将利季娅的作品译入中国,1999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苏联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反思,就提到利季娅,他说:“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出版社出版,我就把它译出来。”
蓝先生曾以日拱一卒的勤勉,一点点写下苏联档案解密后的历史真相,然而终究年事渐高,心纵有余力却不足。在采访中,蓝先生搬出大叠俄文原版书,感慨说:“我若是年轻十岁,那多好啊!”饶是如此,蓝先生却在做一件可能让很多人都惊讶的事情,重新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他说,当年翻译得太匆忙,现在重译,希望能把帕氏小说的诗意最大化地展现出来。
■ 对话
文人的骨气和底气
《新京报》:关于利季娅,你已经在很多文章中都写到了,2001年出版的一本随笔集,题目就是《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那本书前两篇是关于利季娅的,第三篇则直接是你翻译的利季娅的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时隔十年,《利季娅作品选》才出版,你对利季娅感情不浅。
蓝英年:哈,是的。1989年我在俄罗斯教书,看电视看到从美国回来的白银时代的老太太尼娜·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另一位老太太,我就问朋友这位老太太是谁,人家告诉我是利季娅。后来我读了利季娅的《被作协开除记》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极为震撼。这个女作家身上有传统俄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始终听从良知的声音,敢于质疑敢于反思。
可以说,利季娅是反思体制的先行者,比索尔仁尼琴都要早。她继承的,正是俄国自果戈里以来的那种批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她对真相与真理,有一种偏执的热情,把那些当时是群情激奋的会议,都记录了下来。
《新京报》:利季娅和很多著名作家都有交往,比如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并详细地记录了与他们交往的过程和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是否也是你对她的作品有兴趣的一个原因?
蓝英年:首先,当然是利季娅的作品打动我,她在竭力揭露一个被谎言残害的社会,去靠近真相。她与你说的这些作家的交往,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利季娅一家三代都是作家,她的父亲在当时非常著名,因缘际会,她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录者,通过她的日记,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极权的残酷荒诞,和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反抗。
她不仅对外部世界有反思,对自己的反思力度也是很深的,我在文章里也有写到这一点,她曾经说,“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真理会扼住他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灵魂。”她这份清醒,非常可贵。
这本《捍卫记忆》是利季娅的作品选集,我还把徐振亚也拉进来一起翻译,都是“30后”了,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我们选择的原则,就是尽量选择读者熟悉的。其实利季娅还写过很多重要的作家,只不过国内读者不熟悉,我们就没选。
现在谁还会看这么严肃的书呢?不过我的几个30后朋友很激动,邵燕祥啊、朱正啊,都告诉我要写评论。
苏俄历史转变,值得中国更多关注
《新京报》:从苏联到俄罗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这个经历过剧变的国家怎样描述过去的历史,怎样把扭曲的东西回复原样,怎样重新定位历史人物,以及知识分子的回忆与反思,都非常有意义。可惜这方面的译作很少。
蓝英年:我和朱正先生有个集子,名字就叫做《从苏联到俄罗斯》,你说得对,从苏联到俄罗斯,有很多值得中国关注的东西。随着苏联档案解密,我也把兴趣转到了俄苏历史,如果我能年轻十岁,就能做很多事,把一些有趣的书都翻译进来。
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中国是需要去更多地理解它,我知道有些人,比如沈志华,在做一些中苏关系的研究。但是现在精通俄语与俄罗斯文化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读书,读到非常不可思议的翻译错误,真觉得无可奈何。
《新京报》:记得你曾写文章,说有人把斯大林的私人翻译别列日科夫,译成勃列日涅夫,私人翻译变成苏共总书记了。
蓝英年:闹了大笑话。那本书是漓江出版社的《高尔基传》,有趣的是,我后来读别列日科夫的传记时,又发现了不少错误。翻译问题,其实是谈得很多了。前几年,我就说我对译文质量已经麻痹了,这几年还是没见好转。
我觉得主要是社会对翻译不理解,以为翻译是很简单的事情,出版社稿费又那么低,我这次翻译的利季娅作品,出版社给的稿费千字不到一百,哈哈,我在其他地方写个小文章也比这个高点。
怎么提高翻译质量,还真是个问题。我觉得,首先社会要理解翻译这个工作,出版社呢,应该少一些功利心,好的译作是需要耐心等待的。最后,译者自己得有底线。我在俄罗斯教书那几年,就发现在具体的情境中,字面意思和实际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啊。我当时有一个习惯,上街带个本子,听到自己不懂的句子,就请人家在我的本子上记下来。有时听到有人在骂,我也会跑过去让人家把骂人的话帮我写下来。学习语言,就得不耻下问啊。(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