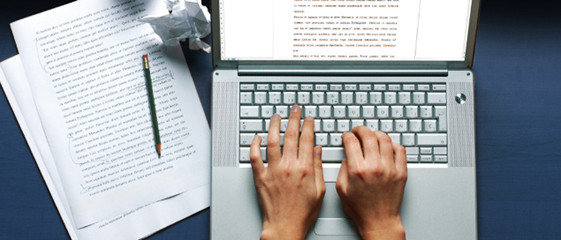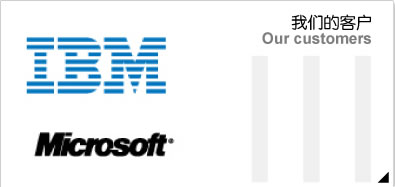羊城晚报记者 黄咏梅
现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发表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200余篇,著作7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 余部,其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等作品,先后十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2008年和2010年两次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傅雷是
前行者的明灯
羊城晚报:您认为翻译家应该具备怎么样的素质?您欣赏的老一辈翻译家有哪些?
许钧:我很尊敬老一辈翻译家,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曾有幸与
季羡林、萧乾、草婴、叶君健等老一辈翻译家进行过对谈,这些对谈现已由译林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对于翻译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觉得也不能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我可以举我非常崇敬的翻译家傅雷为例。傅雷先生一生译作宏富,出版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姨》、《高隆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对中国文化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高超的外语能力,深厚的国学修养,对所译作家作品的理解和爱,严谨的翻译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于我而言,他除了是一个翻译家,更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一生都在渴望光明、追求真理,所以能够与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法国文学巨匠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达成精神上的契合。虽然因为时代的缘故,傅雷先生最终选择安静而勇敢地离去,但他给后人留下了不灭的火种,烛照在历史的天空,成为了后来者前行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出版部门缺乏严密的翻译质量控制机制
羊城晚报:相比起过去,中国人对西方小说的接触越来越同步了,一些出版社为了抢夺市场,及时地买断每年诺贝尔获得者的书籍,造成了翻译速度非常快翻译质量下跌的现象,不少读者时常会发出感慨:“这么差的作品,竟然能得奖?”我想,这里边切实存在着翻译质量的问题,更有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翻译危局”,您怎么看?
许钧:十几年前,我曾就一些翻译问题请教过季羡林先生。当时季老就已感慨“现在翻译风气不好,有的翻译很不负责任”。我想出现这样的现象,必然是有其原因的。自从文化也变成一种产业之后,自从市场对翻译的需求量日增之后,很多人沉不住气,过分贪图眼前利益。我曾听说有些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甚至让不懂外文的人去抄译、剽窃名著。从直接原因来看,问题还是出在图书出版的整个管理机制上,如今的翻译出版部门,没有一个严密、严格、严肃和科学的翻译质量控制机制。
另外,我们也知道,文学翻译的报酬很低,整个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重视不够,导致翻译人才短缺,也令高质量的翻译少之又少。不过我认为,谈论“翻译危局”似乎有些言过其实,毕竟一本译著从开译到最终进入市场,会经过译者、校者、编者的重重把关。而且,随着行业渐渐正规化,中国在文学翻译方面剽窃、抄译的时代也慢慢过去了,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到最后它总会回到正轨上来的。当然这最后还是要依赖整个社会对于翻译的重视。
羊城晚报:反过来,西方对中国作家的作品却并不见得多,记得王岳川在一次讲座里提到过,中西之间的翻译存在的“逆差”非常大。
许钧:这种“逆差”或者说失衡现象既有历史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封闭状态,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主义,包括西方一些国家采取的重扩张轻接受的文化策略,都影响了西方对中国作家的译介。但我们也看到,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文化领域地位的提高,加上政府的重视和中国图书出版机构的积极努力,这架原本严重倾斜的天平也在慢慢回到平衡状态。当然,要实现完全的平衡甚至“顺差”,需要文学界、翻译界、翻译研究界、对外汉语言文化推广和传播机构的努力,也需要不断加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总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翻译速度快并不意味质量差
羊城晚报:有业内人士认为,有的翻译家一年就可以翻译一两本甚至更多的书,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谈谈您的翻译速度吗?
许钧:1978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开始学着做文学翻译,到现在已经翻译出版了30余部著作,差不多也就是一年一部的速度。每个人的翻译习惯不同,每本书的难易程度不同,我想不能简单地以翻译速度来评判译作质量的高低。当然,老一辈翻译家“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执著精神和严谨态度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至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想是如何克服语言、文化障碍,尽可能地忠实再现原作的风格。例如翻译吕西安·博达尔的《安娜·玛丽》,我要处理的是语言结构,博达尔的语言结构十分独特,译成汉语有困难,有的结构(如名词)必须要转译成完整的句子才行。翻译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时,最大的难点在于互文性,书中经常出现前后文以及不同文本的交叉、呼应。他的小说充满反讽和隐喻,具有正话反说和意在言外的特点,这是我在翻译昆德拉小说时遇到的最大困难。至于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难度就更大了,二十几万字,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翻译完。幸好我的有些翻译工作能够得到作者本人的支持,他们给予了我变通的权利。
羊城晚报:翻译如何能做到对原著忠实,又能充分展现出原著的精髓?
许钧:忠实于原著和充分展现原著精髓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忠实于原著并不仅仅是忠实原著单词意义和句子结构,最理想的忠实,是忠实于原著的精髓,或者换句话说,是忠实传达原著的风格。风格问题一向是文学翻译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作者的文字风格是由词语的调遣特征与倾向,句子的组合结构与手段,修辞手段的选择与使用等等表现出来的。所以要再现作者的风格,译者就得从炼字、遣词、造句等方面去做。比如傅雷就认为“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因为他认为“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翻译活动有其主体性,纵使译者有良好的主观愿望,要求他百分之百忠实于原著从客观上来看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忠实与其说是一种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态度。态度端正了,也许不一定能够实现充分展现原著精髓这样的结果,但态度不端正,那么译作一定不会尽如人意。
翻译就像选朋友
羊城晚报:过去的翻译家,一辈子也许就翻译一位作家的作品,您也说过,翻译一个作家的书籍,不仅仅是翻译,而是在研究,您研究的西方作家中,最喜欢的有哪些?
许钧:翻译一部书就像是在选朋友、交朋友。我们和人交朋友,自然应该努力去了解他,翻译也是一样的。我每翻译一部书,都会进行思考,最后有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是翻译带给我的另一种意义和价值。我翻译了托多洛夫的《失却家园的人》、米歇尔·图尼埃的《桤木王》和昆德拉的《无知》等作品后,都有感而发,写了一些研究性文字。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产生了系统研究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状况的念头,现在这个念头已经变成了《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这本书。在翻译和研究过程中,我常常会和作者本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我和吕西安·博达尔、艾田蒲、勒克莱齐奥等就是如此结识的。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是我很喜欢的西方作家,1980年我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他现在不仅是我所译的作者,我所研究的作家,也是我的好朋友。
羊城晚报:曾经有网友对比过您和作家韩少功翻译的米兰昆德拉的那本书,韩译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您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作为专业的翻译家,您认为作家翻译与翻译家翻译有什么差异?
许钧:作家翻译与翻译家翻译的差异,我觉得很难从类别角度出发去谈。但这个问题也折射出普通读者的一个观点,即人们常常会认为作家翻译似乎能够保证文采,但忠实度可能差强人意,而翻译家翻译似乎能够保证忠实,但可读性就不如作家翻译。我是不太赞同这种观点的。首先,中外历史上很多作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翻译家,其次,作家翻译也有不同的倾向,比如鲁迅倾向直译,而法国著名作家波德莱尔在翻译爱伦坡小说时,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改写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地看。以我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经历为例。那段时间,我与韩少功先生有过交流,他对翻译问题,例如忠实性和创造性等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两个译本的差异,主要还与时代因素、个人的翻译观、个人风格有关。时代所提供给韩少功的翻译的可能性跟我翻译时的可能性不同。他翻译这部小说是在 1987年,在那个时代,需要避开很多表达方式,对有些段落甚至不得不进行删改。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拥有更多的自由度。正是因为时代有别,翻译出来的作品也会有所不同。另外,每位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表达时也会有不同的风格。
苏童小说法译本
有不少翻译误差
羊城晚报:我了解到,现在不少中国作家也有作品被翻译到西方,但是基于汉字的复杂性,您认为这些翻译的准确程度如何?
许钧:翻译活动首先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语言符号不能孤立地来看,一种语言符号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意义生成系统,它身上积淀着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全部文化。所以与其说是语言的差异造成了翻译困难,不如说是文化的差异从根本上造成了翻译困难。参照体系一变,文化语境一变,一部作品的意义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一变,其面貌必然发生变化。比如苏童小说法译本的翻译误差,我们曾提到,《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这样的翻译误差无疑会导致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风格的流失。但这些误差与其说是汉语的外译难度造成的,不如说是译者和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因为一部小说、一种文化在域外的译介和接受过程很不简单,它涉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之间的碰撞。反过来说,误差的存在虽然造成了遗憾,但我们也应看到,翻译活动绝不仅仅是字面层次的语言转换,而应是思想的转渡和文化的移植,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转换并不比欧洲语言之间的转换更为复杂,而且谈论符号间的准确对等是没有意义的,德里达就曾说过,如果只从符号角度来看,翻译根本上是不可为的。我想比起拘泥文字间的对等,翻译活动更该注重其所承载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维度。
女作家池莉在法国
很受欢迎
羊城晚报:您所了解到的国内作家在国外的出版发行情况如何?
许钧:我对国内作家在法国的出版发行情况比较了解。中国古现代和当代典作家在法国的翻译情况,我指导我的一些博士生做过一些研究。从鲁迅、巴金、老舍、郁达夫等现代文学作家,到王蒙、陆文夫、张承志、莫言、韩少功、王安忆、黄蓓佳、苏童、叶兆言、王硕、余华、毕飞宇、池莉等当代作家,已经有很多作品被译介到了法国。据一些研究者统计,截止2006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法译本包括复译本在内约145部;在当代文学方面,1980年至2009年期间,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有三百部左右。随着法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渐增,我想这个数字应该会呈递增趋势。法国有一些专业引进中国图书的出版社,例如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南方书编出版社等,都在为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作出积极的努力。但与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相比,法国对中国作家的译介一是译书种类少,二是译本发行量少。通常一个译本如果不再版的话,也就是几千册的发行量。池莉是近几年在法国译介得比较多的中国作家,她被翻译成法语的八部作品,包括再版本在内,在法国的总销量达到了七万多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