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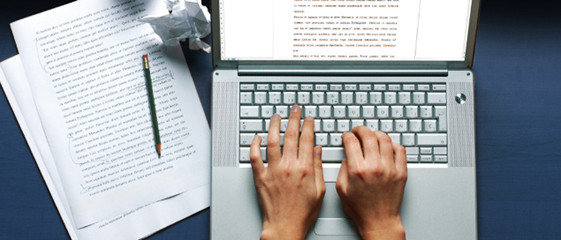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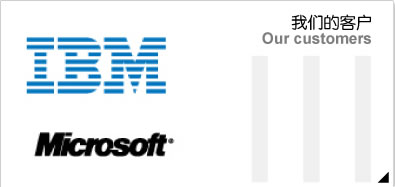
范晔:阅读是快感,翻译是自虐
发布时间:2011-08-01 09:11:32 来源:ACME 转载 字体: 大 中 小
2011年夏天,正式获得马尔克斯授权的《百年孤独》在中国出版,也如老马形容的“热香肠”一样热卖,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百年孤独》中文译者范晔之前并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热闹景象,有人为庞大的布恩迪亚家族绘制家族谱系图,有人激烈地讨论范版译文与之前黄锦炎、高长荣等版本的细节差异,有人用各自所长的语言看各语种翻译与中文翻译的区别,也有人从当前译本中回味多年前初读《百年孤独》时的记忆。
范晔坦言,在接受翻译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对这本书心怀期待,也因此,他在微博行开了一个“羞愧集结帖”“专门收集本版硬伤,特别是不可饶恕的那种。”
不过,在斑斓多姿的拉美文学中《百年孤独》只是其中的一部,虽然能与它比肩的作品不少,范晔说能有那样的影响力的,也许只有这一部。他主攻的领域是拉美诗歌,诗歌研究及翻译在西语界寥寥无几,“拉丁美洲精彩的东西太多了,需要介绍的太多了。”说起那些应该被译介过来的拉丁美洲诗人时,这位年轻的学者有些兴奋,“你看像莱萨马·利马(Jose Lezam a Lim a),偶像级的,他写诗,但是他有一本很牛的小说《天堂》,也有人说他是‘拉美的普鲁斯特’,非常值得做一做!”范晔说自己暂时可能不会再翻译小说,但真如果翻译莱萨马·利马的书的话,他恐怕会动心。“如果要译他的书,得去古巴待上一年半载的,找一些高人来请教。”
我想尽量少伤害别人对这个书的感情
南都:《百年孤独》你最早读的是吴建恒的译本?
范晔:对,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南都:还有印象吗?
范晔:没有什么印象,没有觉得特别的震撼。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一个人和一本书相遇的这种机缘,有的时候是讲究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书,有的时候你要是机缘不凑巧或者缺少一些什么,可能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是有一点,很多读者对这本书的热情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而且都是大家一些成长经历或者阅读经历中非常重要或者印象深刻的一部分,这个我也是没有想到。
南都:你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专门征集大家挑错?
范晔:我之所以这样发帖想挑硬伤,无非就是想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再打磨得好一点。有些东西你说整个风格你不喜欢,这个我改变起来比较困难,你让我换一个别的,那就不是我了,此时此刻这种情境下我能给出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一些漏译、错译或者现在想起来处理得不是非常妥当的地方,或者能想起更好的表达方式,尽可能地把它打磨得稍微更好一点,这样也对得起大家对这本书的感情,我主要是这个考虑。
其实我本来是想一本书翻完了我就可以撤了,顶多就是你偷偷地看一看人家夸你你就高兴一下也就完了。但是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尤其它涉及太多人的感情,因为它是你经历的一部分,你记忆的一部分,这个东西我还是非常尊敬的。因为一本书你文学史的评价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有变化。但是我特别看重读者对书的感情,作为译者,我本来就是读者。所以我就是想尽量少伤害别人对这个书的感情。
我不希望出现非常重的所谓的翻译腔
南都:可能很多人最初读到马尔克斯时,对他的文风记忆深刻,那种瑰丽奇谲的面貌是之前特别陌生的,还有人甚至记得马尔克斯的那种独特“气息”,所以会有人评论说“相见不如怀念”,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范晔:这个挺复杂的,用这个词的时候每个人可能想说的东西不一样。因为它可能就是跟你的某一段记忆和经历连接在一起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你会把你对拉美的这种想象、这种期待又和某一种文风联系到一起,这样你看到其他风格表现,你可能觉得失望,沮丧,或者是愤怒,因为它冒犯了你的一些记忆。这个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也是一个读者,我也读一些其他的译文。这个也没关系,我想每一个译作都是有相对的自足,而且对一个经典来说它也不怕再重译,再说译本这个东西又没有什么定本可言,你看从1984年到2011年,这过了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用不了二三十年可能又有新的译本出来,至少可以取代我的译本,大家可以有更多新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像《红与黑》都有十几个译本。
南都:陈众议觉得你的翻译是“异化”的,把读者直接带到作者那里,但是也有评论觉得你的译文缺少那种陌生感,中文很好,打磨得太光洁,好像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
范晔: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一切所有的翻译都是在规化和异化中找平衡点,因为翻译本身是一个妥协的艺术或者说是一个平衡的艺术,永远在张力之中,但是要在张力中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一个动态的平衡。所以我倒也没有觉得我这个特别规化或者特别异化,我倒没有主动去追求它。可能战术上局部上稍微有一点,我个人有一种观点,就是小说可以考虑得规范一点,但是诗歌要异化一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马尔克斯的文风有时候很多变,比如说局部明显有一些语言游戏,有些地方它是向以前的文本致敬的,所以这种地方我为了体现这种东西,就是稍微使它变得异化一点我也在所不惜,但是整体上我主要是想还是回到那个调子上。因为我觉得马尔克斯原文的语言掌控得很好,我作为一个读者印象太深了,翻译有这种动态对等的原则,就是一个西语的读者读马尔克斯的时候不会读出这种很生硬的东西,我们汉语的读者也应该有大约相同的一种感受,我主要是从这方面考虑。或者当时也可能受到一些前辈的影响,像弗雷西尔,他说译者应该想象如果原作者用中文写作会怎么样,另外搞法语的罗新璋先生说“译应该像写”。当然马尔克斯用中文写作是怎样,我肯定也没有这个能力达到,但是我可能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所以就不希望出现所谓的翻译腔非常重的。可能有些读者恰恰是期待翻译腔,不过这也很正常,因为任何一个作品包括译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那么没有达到人家的希望我也很抱歉。
南都:在具体翻译中哪些方面的困难比较大一些?
范晔:(笑)大家都问我困难。困难可能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像前面说的希望找准基调,另一方面是具体的困难,像很多对中国读者比较陌生的文化符码,包括一些名物,那就查工具书,网上查,还有就是向拉美的外教请教。
南都:也有读者比较纠结“里正”这个翻译。
范晔:“里正”我自己也不觉得处理得好,之所以这样处理,其实是想保持里面双关的语言游戏,当然你把它翻译成“镇长”也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双关语就没有了。小说里面有个上下文,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们本来是生活在一种准乌托邦的田园牧歌式的环境里面,原来是自治的,但是突然就出现了“政府”这样的东西,政府派来这样一个人,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实际上不认识corregidor这个词,这个词字面上看,是从动词corregir“纠正”这个词过来的,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官职的意思,他望文生义觉得是“纠正者”,所以他说“我们不需要纠正者”。它不仅仅是语言游戏,也代表了马孔多人这样的一种心态。当然这里面又隐含了整个《百年孤独》的一个主题,解码的主题,里面有很多编码与解码,羊皮卷是最明显的,还有其他的,比如有很多黑话,像小女孩丽贝卡来的时候,她说的话别人不懂,西班牙语她听不懂———其实她懂的,但她不回答,但是说印第安人土话的时候她又懂了。里面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解码、误解码、编码,这个小小的细节也体现出来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也解码错误,他没有看到corregidor真正的意思,他字面义理解成“纠正者”,所以会有这样的话。如果翻译成“镇长”的话后面怎么翻呢,这个语言游戏就没了,当然你也可以加注,我也加了注,你只能加注说明,“镇长”和“纠正”的关系,如果能在翻译出这个来当然更好,所以我为什么翻译成“里正”呢,是希望“纠正”的“正”能和它联系起来。
他把自己当做一个小说的形象来创作
南都:有评论包括马尔克斯自己的现身说法,说《百年孤独》的写作风格和马尔克斯其他作品相差也是挺大的,有的是非常简洁,可能会用新闻式的那种方式,但《百年孤独》看上去似乎华丽、繁复,这本书在他整个写作当中的风格特点是怎么样的?
范晔:我不是研究这个的,也没有整体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包括马尔克斯前期的作品在内。咱们老感觉《百年孤独》非常华丽、繁复,其实它是很多样的,很多时候也不是从头到尾都很华丽、繁复,我并不觉得。有些描写他不惜笔墨,但是有些时候叙述也很简洁。或者有人说巴洛克式的,马尔克斯绝不是巴洛克式的,在文学史中,说到拉美的新巴洛克,我们都不会用在马尔克斯身上,我们会把新巴洛克的标签用到卡彭铁尔、莱萨马·利马这样的作家身上,但起码在我狭窄的阅读经验里面,没有看到文学史家把这个概念用在马尔克斯身上,他至少不是最典型的,即使《百年孤独》我觉得也不是。
南都:翻译中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范晔: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马尔克斯对语言的操控能力,这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体现这个叙述者的基调,我就对这个印象非常深,我希望能够把这种东西再现出来。所以“27年一代”的纪廉就说马尔克斯像上帝一样写作,说“像上帝一样写作”就是他能够很精准地控制所有的喜怒哀乐,而且用最经济的笔墨,当然该挥霍的时候他也不吝啬挥霍,但是他都能控制得非常好。我一直读马尔克斯也是这种“天地不仁”,一切都把握在手里的感觉,这也是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当然他是艺术大师那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这次重新读也觉得之前稍微有点偏见,有点太片面了。他有极强大的控制力,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完全冷漠的或者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那种态度,这两者并不是绝对不能共存的,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细节能够读出他的温情。只不过他的不是那种直接性的或者很抒情性的流露。所以这也是我一个新的阅读感受。
南都:对于《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自己对它的评价是,从文学角度来说《百年孤独》并不是他觉得最得意的一个作品。
范晔:是,但是马尔克斯说话你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神话制造者,马尔克斯本身就是马尔克斯制造的一个形象。他有这个意识,起码我有这种感觉,他在各种访谈中,特别是在他八十年代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觉得他的访谈中有一种游戏在里面,他有一定策略地、有意识地在营造他自己,他把自己当做一个小说的形象来创作,所以他说话你不可以全信,他在跟你做游戏,你要是太当真你就失败了。(笑)
翻译大多数时候带来挫败感
南都:你觉得翻译这本书和之前翻译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哪些体验是特别不一样的?
范晔:肯定不一样,因为这是两个精神气质完全不一样的作家,虽然他们俩都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科塔萨尔不是另开一个天地出来,他没有马孔多世界这样一个另外的现实,他是把习见的日常现实生活给你偷偷地打开一个裂缝,给你找到一个罅隙出来,你说非现实也好、另一种现实也好或者幻想因素也好,它都恰恰隐藏在现实中,或者跟你的现实因素是纠结在一起的。你想他的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两个城市,一个是巴黎,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偶尔有哈瓦那什么的,基本上没有别的地方,所以他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南都: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就是写堵车,写得让人很吃惊。
范晔:对,你不知道他从哪一分钟哪一时刻把这个现实给你扩展了,或者给你打开了一个传送门,你不知道从哪一时刻他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点。所以两个人都是很厉害的幻术大师,但是路数完全不一样。
南都:读者和翻译者这两个身份,在你翻译这个书的时候两者之间会打架吗?
范晔:其实肯定也有一定张力,因为作为读者还是很高兴的,你读科塔萨尔也好,读马尔克斯也好,确实有阅读的快感。但是阅读是快感,翻译就是自虐了,就是痛并快乐着,有时候恰恰阅读时给你制造极大快感的东西,在翻译中可能给你带来最大的痛苦。因为有些东西你觉得这个写得太漂亮了,太好玩了,但是有的时候“妙处难与君说”,这种东西恰恰是很微妙的好处,你恰恰可以很会心地领会到,但是你怎么把这个东西传达出来就费劲了。当然你要是能够很幸运地想到了一些再现的方式,那么这种成就感也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时候是一种挫败感。
采写:南都记者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