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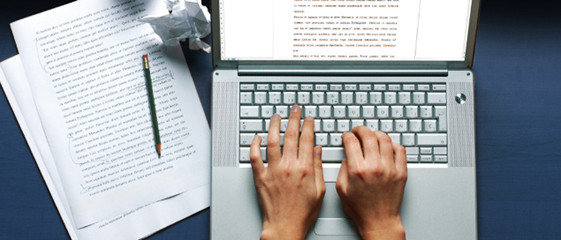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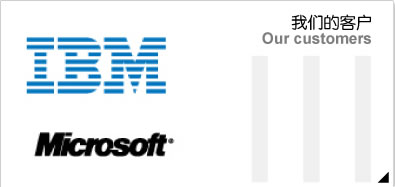
傅雷翻译文学经典与中国现代作家
发布时间:1970-01-01 08:33:30 来源:ACME 转载 字体: 大 中 小
在近代文学翻译界,傅雷先生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卷帙浩繁、技艺精湛的译品而被批评家誉为在中国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的翻译大家。他毕生致力于中法文学艺术交流事业,把法国经典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洋洋500余万言。他在其中用力最多的是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两位大师的小说。两者相较,如果说巴尔扎克译品是“傅译浩瀚天地中的重镇”,若从接受与影响的精神层面来考量,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则是傅雷翻译世界中拔地而起的一座丰碑。这是法兰西文学巨子罗曼·罗兰和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傅雷用心灵、智慧和激情所共铸的一座洁白的丰碑。
傅雷生前谈及自己翻译经验时,曾说过:“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傅雷来说,可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朋友。傅雷与他们的相遇,是20世纪中法文学交流史中的“奇缘佳遇”,是热爱真理、追求光明的中国弟子和法国导师的心灵相遇。我们知道,从译介学学理层面看,译者是作者的代言人,他负有在本土文化圈内诉说作者心曲、延伸原作文本生命、拓展原作生存空间的使命。傅雷之于罗兰,从其相通的心智和气质、相似的性灵才情、相近相匹的学养和热情,以及傅雷精湛的技艺和上佳的译品,都不难看出,傅雷是罗兰在中国的理想而忠实的代言者。海峡两岸凡是读过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读者,面对这部“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文本,亲临过那行云流水、色彩丰富的文字和流淌在字里行间那股炽热的激情和精神气韵,品味过那“江声浩荡”的警句和恢弘瑰丽的乐章,都会从中获得一种真与美的心灵熏陶和洗礼。当他从阅读中走出来的时候,都会感到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增添,都会情不自禁地与克利斯朵夫这个闪烁着强奋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清新的灵魂”拥抱得更为亲密,因而都会从心底里发出一致赞叹:多亏了傅雷以独有的才情、睿智和激情的参与,才使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不朽巨作在东方这块拥有最多读者的大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傅雷才是罗兰不辱使命的最佳代言人,这不是需要人们来探讨的学理,而是不争的事实和共识。罗兰和傅雷珠联璧合,原著和译作先后辉映,这的确是近代中法文学与文化关系史册值得一书的佳话。
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由傅雷脍炙人口的译介而成为翻译文学经典。灌注了作者与译者生命激情和精神理想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在70多年风雨兼程的中国之旅中,成了“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和无数青年读者所追奉的新人形象,对中国现代知识界和新文学作者文化人格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借助傅雷翻译文学经典流入中国,最使中国接受者振奋的,莫过于克利斯朵夫这一向真、向善的灵魂所投射出的罗兰精神。何谓罗兰精神?这就是为人类之大爱、为自由和真理而搏斗所折射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格力量和英雄主义气质——我称之为罗兰精神的三根支柱,它也是傅雷精神的体现。罗兰说过:“人道、自由和真理——这是宝中之宝”,是“最崇高的道德价值”,是生命的“神祗”,他创作的目的,“在于将人从虚无中抢救出来,在于不惜代价地给人灌输魄力、信念与英雄主义”。对此,傅雷心有灵犀,他对傅敏说过:“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为立身的原则。”他译介罗兰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支撑,引进“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罗兰的精神内核,令人联想到儒家“仁学”结构中“爱人”的人道精神,注重道德修养的人格追求和舍生取义的历史责任感。无怪乎傅雷译介罗兰要征引孟子的警句作为译文的献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由西方文化所培育的罗兰精神和由儒家文化积淀的中国民族心理结构之间的某种相似和契合,在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中国作家之间构架了精神沟通的桥梁,而这座精神会通之桥,是由伟大的罗兰和卓越的翻译家傅雷共同架设的,傅雷为构筑这座联系东西方贤智的桥梁,不惜以身殉职,最忠实地履行了罗兰一个时代的“精神遗嘱”。
在罗兰精神中,最能激起中国接受者心灵震撼和精神共鸣的,是罗兰在探求真理、追求人性至善的逆境中奋勇搏击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对中国知识群体,特别是对在黑暗中苦斗求索的中国新文学作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早在192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就在他主编的《莽原》译出日本作家写的《真勇主义》,率先向国人介绍了罗兰的英雄主义精神。此后,随着傅译罗兰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流传和克利斯朵夫与中国读者“拉手”,我国不少作家,如巴金、胡风、路翎、萧军、白桦等,便不止一次提到它,不仅把它视为生存哲理加以崇奉,而且把它作为看待人生、探索人生的一种准则,助成了一代求索者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文化人格建构,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在中国新文学作者看来,罗兰的英雄主义首先是直视人生的“大勇者”的战斗精神。白桦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撰文指出,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集中体现着这种英雄精神,赞叹他在人生攀登中,“踏碎横在自己前程上的障碍,不惧怕、不避免任何艰难,直视人生,深味着人生,没有妥协,没有虚伪,片刻不停地时时和困苦艰难战斗”,堪为榜样。对于一个执着于人性开发的文学家来说,直视人生的战斗精神,其实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萧军在1945年发表的《大勇者精神》一文中,第一个将罗兰的大勇者的精神与鲁迅的那种“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直面人生的战斗精神,将罗兰的英雄主义和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联系了起来。萧军认为罗兰的“ 大勇者精神”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便是“真诚”二字,“真诚的感情,真诚的思想,真诚的美和力量”,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执了这‘真诚’底从诸种悲苦、困厄、堕落、失迷……而冲杀出来的。而作者底一生也正是用了这‘真诚’底剑,醮了自己‘真诚’的血液,冲杀过来的一人”,这种对“真诚”的强调,完全与中国新文学作者致力追求的“真的文学、人的文学”是相通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那些主体意识强烈、个性鲜明的作家如路翎、胡风、巴金等,正是沿着这条路子,从罗兰那里汲取思想滋养和文学滋养的。
在中国新文学作者中,真正把握到罗兰的英雄主义与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理论上加以开发的是胡风,在创作上加以实践和拓展的是路翎和巴金。胡风读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迷恋罗兰的英雄主义,赞叹罗兰创造出“那为善而受着痛苦的灵魂”,以此来“救援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样在孤独和寂寞中间作战的痛苦的兄弟们”,来“照亮他自己身受的腐朽的世界和困乏的人生”(胡风《罗曼·罗兰》,1941年)。胡风感到,罗兰笔下的一些受难的灵魂之所以具有一种魔力,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就在于真实,“真实就是生命,历史的真实只有溶进战士底伟大的性格而被发现出来以后,才能够成为精神的力量。”罗兰创造的这些“伟大的性格”和真实的、“受着痛苦的灵魂”正是罗兰的英雄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胡风明确地指出,罗兰的英雄主义通过中国精神界之战士鲁迅,“俯向了中国人民的苦难”,“燃烧在克服苦难、争取自由的人民里面”(胡风《向罗曼·罗兰致敬》,1945),他清楚地看到了罗兰的英雄精神在中国滋养民心、滋养文心和振奋民气的重要作用,因而更深刻地捕捉到了罗兰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鲁迅现实主义精神内脉相通,并助成了他对写出真实人生、写出人生真血肉的“灵魂现实主义”之思考与探索。
路翎对罗兰精神的崇尚,直接引领他创造出中国式的克利斯朵夫,他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我在当时,是很欣赏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内容是当代的人生追求和当代的人生现实之间的斗争内容。我在写《财主底儿女们》的时候,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伴我走过这段行程。”我们在他这部小说男主角蒋纯祖身上,确实见到了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他们都具有不寻常的“雄心和梦想”,幻想建立奇功伟业,都企图跨过“混沌的生活”,追求阔大、自由的人生,都是“漂泊者”,都骄傲于“漂泊者”的那份“孤独”,都有着“内省”的狂热癖好,都不乏“光荣的、高贵的”自我意识,都表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这些相似都深深地打上了罗兰英雄主义的印记,表明倾心于英雄气魄的路翎是怎样深切地显示着罗兰的精神特质。以致他笔下的这个蒋纯祖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比肩而立,成为日后一些青年读者的“ 不可分离”的“知己”与“伴侣”。
将罗兰的英雄主义和战斗品格升华为生命意识和创作的主体精神,并由此开创了人品与文品谐和一致的中国新文学一代风范的,是巴金。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在提及外来文学滋养时,从未回避罗兰给予他的这种特殊的影响。他在1940年代给法国汉学家明兴礼博士的一封信中曾这样明确地说过:“我喜欢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比方他所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三部传记、大革命戏剧。他的英雄主义给了我很大影响:当我苦闷的时候,在他的书中我常常可以寻找快慰和鼓舞,他使我更好地明了贝多芬的由痛苦中得到欢乐。靠着他,我发现一些高贵的心灵,在痛苦的当儿,可以找到甜美,可以宰割住我的痛苦,他可做我们的模范和典型。爱真、爱美、爱生命,这是他教给我的。”在这里,巴金显然是把罗兰及其英雄主义视之为人的“楷模”和为文的准则加以接受的。正像罗兰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往往不可分割一样,集作家、战士于一身的巴金,为文的原则和为人的原则也是二而一体的。当他从罗兰那里学到了“爱真、爱美、爱生命”的品质时,事实上他也获得了一种为文的准则,巴金的全部作品可以说都是这“爱真、爱美、爱生命”的颂歌。这是巴金受惠于罗兰英雄主义人品和文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