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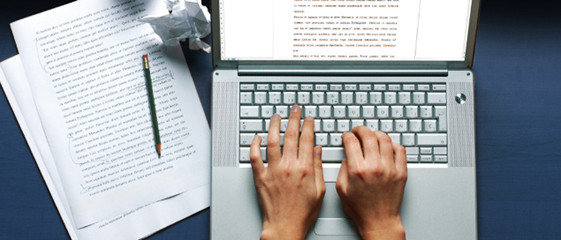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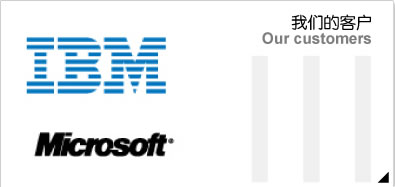
没有比翻译五经更紧急的事了
发布时间:1970-01-01 08:33:30 来源:ACME 转载 字体: 大 中 小
经过一年的启动筹备,大型国际汉学合作项目—《五经》翻译工作终于正式开始了。
除了《毛泽东选集》的外语译本,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本著作的翻译能和《五经》翻译的规模、声势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大型的翻译团队,世界各地的学者济济一堂,为将《五经》准确地翻译成外语而出谋出力,而这个大型国际项目的主持人正是蜚声国际的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先生(Kristofer Schipper)和他的妻子袁冰凌教授。
利玛窦译中国经典已有400年
翻译《五经》的历史在西方也是源远流长。
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理雅格(James Legge)翻译成英文的部分《五经》可能是《五经》翻译史上最出名的一个版本,他将这些书称之为“中国经典”。瑞典汉学大师高本汉对于理雅格翻译的《诗经》并不满意,他指出,理雅格基本上遵从朱熹之说,同时也偶尔附和其他各家的解释,但是他很大程度上疏忽了清代语文学家的意见,所以在高本汉看来:“他的很多观点过时了。”
不过,和另一位《五经》翻译大家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比较起来,理雅格恐怕还不算是朱熹最虔诚的信徒,高本汉认为顾赛芬的所有观点几乎都照搬朱熹。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事,因为对于这些具有拓荒性质的西方汉学学者来说,最便捷而不至于迷途的路径就是利用中国古老向导的指点。
如果把《礼记》中节选出来的《大学》和《中庸》篇都算上的话,西方人翻译《五经》的历史已经有400多年了。自从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将《四书》中的《大学》大部分翻译成拉丁文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就开始走上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典籍的艰难旅途。罗明坚曾经的助手利玛窦—他当时在中国广东的肇庆在做着同样的事—对于这位同行和前辈的汉学水平显然有一定的怀疑,他于1596年12月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明确说:“罗明坚的译文并不是好的,因为他只认识很少的中国字。”博学的利玛窦有这样的自信,他的光芒终于盖住了罗明坚,这位被《四库全书》收入七部著作的意大利神父也翻译了《四书》,并把它寄回了欧洲。
“我们中国的经就没有了吗?”
施舟人先生当然也有一种中国情结。他的中文名“舟人”让人联想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摆渡人。这个摆渡人的角色要追溯到57年前。1952年,荷兰国立博物馆举行“远东美术展览”,内容包括中国和日本各个时代的艺术品。很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这家博物馆,空山灵雨的山水画、温润如玉的瓷器、还有最让他目瞪口呆的青铜器。那一次,他怦然心动:定了,去巴黎学习东方艺术!
就是那么简单的缘由,他从荷兰远赴巴黎,到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学校读书。
多年后他成为西方汉学界研究道教史的大家。《五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怎么会进入他的眼帘的?这话说起来还要追溯到他的挚友饶宗颐先生的一段心结:“有一次,法国教育部和文化部出了一笔钱,有一个大的出版社希望出一套世界经典文库。他们把这个计划发给饶公看,有以色列的《摩西五经》等等,他们找的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学性作品《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等。他就有些不高兴,他说:‘怎么可以呢?我们中国的经就没有了吗?’”传说饶宗颐教授为此落下了眼泪。
尽管《五经》翻译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是现存的版本芜杂、翻译水准参差不齐,最主要的是没有一套可以通行的译本行世,这直接影响了西方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思想的了解。年届八旬的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教授汪德迈在《五经》翻译的工作会议上更是大声疾呼:“现代文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多语种翻译中国《五经》更紧急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施舟人的心中埋下了重新翻译出版《五经》的念头,当他向国家汉办(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得到了国家汉办的热情支持。2008年,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知名学者和汉学家,涉及海内外经学界、训诂学界、考古学界、翻译界等领域,真可以说是一个旷世的文化大工程。
对话
施舟人:我不伟大,但我可以做一叶小舟
多年前无法去城隍庙烧香
时代周报:您18岁时第一次接触中国。那是1952年,荷兰国立博物馆举行《远东美术展览》,内容包括中国和日本各个时代的艺术品。您就对中国的青铜器、瓷器和山水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与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是这样的吗?
施舟人:一晃57年过去了。那时荷兰国立博物馆举办了《远东美术展览》。荷兰这个小国家虽然和东亚的联系很多,但是在荷兰收藏的中国艺术品比较少。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些中国艺术品在荷兰很难看到,其一就是青铜器,但是那一次我就看到了青铜器,虽然我不记得当时展出的是商代、西周还是东周的青铜器(可能是商代的)。当时青铜器在欧洲少之又少,因为中国解放以后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好,很多青铜器都是那时候发现的,就比较少流到欧洲。那次展出的还有一些中国绘画,也让我为之着迷。
时代周报:后来怎么会在中学毕业之后离开阿姆斯特丹,到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学校读书,同时学习中文的?
施舟人:二战结束后,我父母很快就不在了,正好当时有一个去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学校读书的机会,于是我就去了。
当时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学校有关于中国美术史的教学。我们学院的学生并不多,我的老师鼓励我去学中文。一开始我不是很有信心。那时欧洲的学校学费不很高,高等教育也很自由,你要读什么书都可以,于是我开始在巴黎大学学汉语。虽然巴黎为欧洲文化、学术、艺术的中心,可是法国人一般来说对外语不怎么感兴趣。所以我有一点优势,我从荷兰来,荷兰是小国家,有学外语的习惯。
我记得当时在巴黎大学一年级学汉语的学生只有8人,和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半个世纪前,欧洲的中文教学很少,而现在法国大部分的中学都有中文课,而且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开始在欧洲设立分校,对此我觉得很高兴,中国文化正在逐渐被世界认识。可以说,我现在正在主持的《五经》翻译项目,也是推广中国文化的一种方法。
时代周报:1979年中法两国恢复友好邦交后,您马上就动身来北京进行研究工作?
施舟人:1975年,我和欧洲汉学界的同仁在巴黎创办了“欧洲汉学学会”。1979年我那时代表欧洲汉学学会邀请钱钟书先生和夏鼐先生到欧洲来访问。因为社科院也刚刚成立了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先生也请我到北京访问。我和任继愈先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很遗憾他已经过世了。我和季羡林也认识,但没有那么熟。任先生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人在中国现在都是很好的学者。
时代周报:当时刚刚文革结束,您看到的中国是怎么样的?
施舟人:1979年我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到上海的时候,我很想看有名的上海老城隍庙。那时城隍庙刚在维修,庙前面的戏台还有人居住。我当时不能到城隍庙里面烧香,拜城隍爷。现在城隍庙恢复得很好,去烧香当然不再是件难事。
今天的翻译很苦但很值得
时代周报: 《五经》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您的中文名,您说:“因为舟人就是渡人,就是要做过渡的事情。”所以您很早就要学习汉学,把您的志向定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上?
施舟人:这是偶然的,我的荷兰姓叫Schipper,和英文中的skipper一样,是船长的意思。中国已经有一个王船山了,我没法跟他比,没有王夫子那么伟大,我只可以成为一叶小舟。
时代周报:我知道1962年到1970年之间,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在台湾您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中国传统的民间香火组织及其活动?
施舟人:葛兰言说信仰和社会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有道理。比方说,目前香港人的黄大仙香火可以说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是这个香火的历史非常悠久。其实黄大仙就是赤松子,从汉代开始就有这样的信仰,山东地区、沿海地区一直到广东原来都有赤松子的庙,所以这不是小事情,也不仅仅是民间的事。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陕西宝鸡的陈宝夫人的香火。这个香火从西周一直不中断地延续到现在。从文化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可以更注意这个很有特色而且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还活着的信仰传统。
我们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五经翻译”项目会议上,一些学者也谈过这个事。比如北京的天坛已经成了一种建筑遗存,但是在民间还保存有许多跟古代礼仪有关的仪式。
时代周报:您2003年出任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暨西观藏书楼主任,怎么会选择定居福州?和您夫人袁冰凌女士有没有关系?
施舟人:袁冰凌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她后来在厦门大学任教。因为学术交流,她到荷兰做访问学者,并得到莱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后来福州大学很想发展文科,请袁冰凌担任新建的文学院副院长。我们在福大培养了一些研究生。我发现中国没有什么西方人文科学方面的图书馆。我自己的书不少,荷兰教育部给了我一笔启动费,于是袁冰凌和我就建了一座西观藏书楼。后来国家汉办知道了,开始和我们发展“五经翻译”项目。
时代周报:您是非常著名的道教史研究学者,怎么会来翻译儒家的《五经》,您觉得翻译《五经》有怎么样的困难?
施舟人:将《五经》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首先是在1979年由饶宗颐和我共同提出的。有好几次,我们向学术和研究机构提出这样一个计划,但都无功而返,后来我们也曾以福州大学西观藏书楼的名义申请学术项目计划,但是同样没有获得成功。2008年的春天,这个项目向北京的孔子学院总部提出后,经过一个中外学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评估后被通过了。
我们有理由说《五经》在当下需要再翻译。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了,翻译《五经》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首先我们要翻译英译本,尝试将它的本义梳理清楚,避免它不要受到一些古代儒家学者注释的影响,同时既要注意翻译的准确性,也要注意它的可读性。这绝不是说翻一遍就可以结束任务的,很苦,但是很值得。